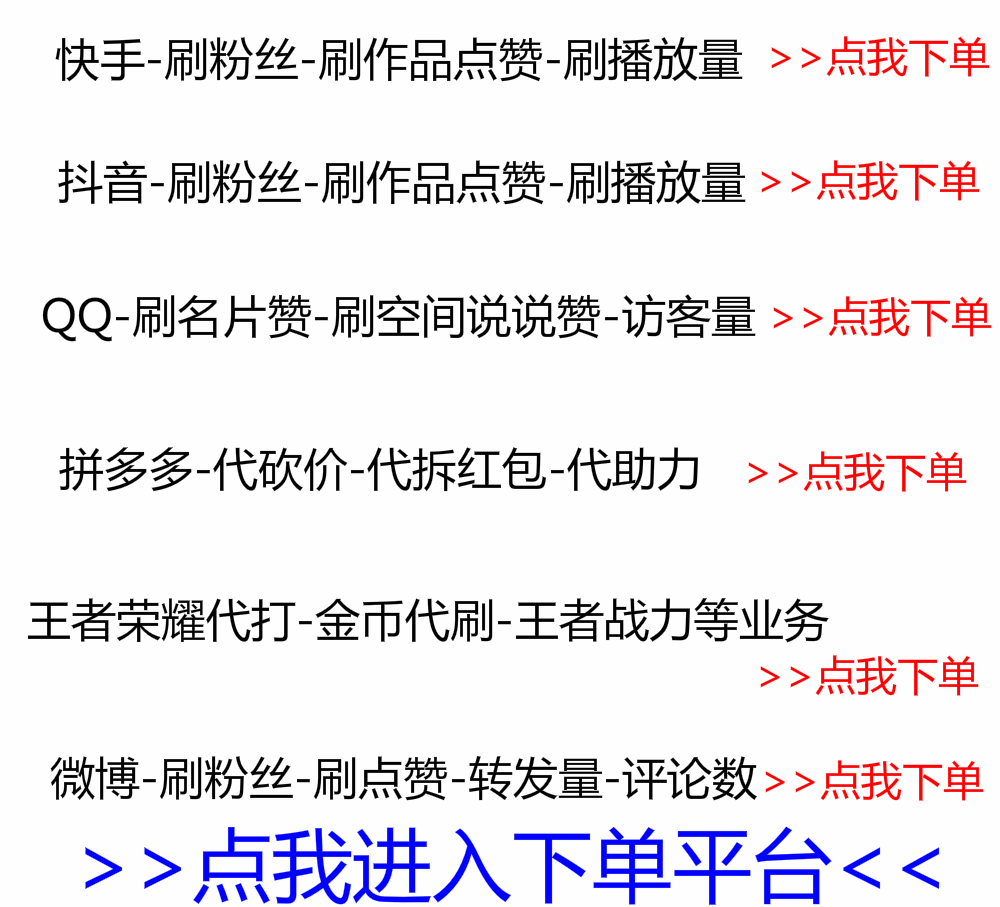
文:舒仪
时间过得飞快,距离《曾爱》这个故事的问世,转眼早已六年了。
十年前,我还在国企,每天穿着职业装打卡下班,每天想得最多的问题是:
如何能够搞定哪个最难缠的顾客?或者怎么赶跑所有的竞争者得到那种梦寐以求的位置?又或则年末的业绩评估能不能得到优秀?年初的加薪可不可以领到理想的额度?诸如此类。
我以为我会顺着这条路仍然走下去,然而人生的转折,总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等着你。
十年前我绝对不会想到,有三天我会离开熟悉的写字楼,成为一名专业写作者。
假如时间再向前溯源六年,我更不会想到,一个标榜从不相信感情的人,竟然能在若干年后专写情感小说。
不得不说,人生的境遇和轨迹,从开始到结束,都不是你自己所能控制的。生命总是饱含了不可思议。
而这一切转变,都是由于我写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子,起初叫《我记得那美丽的刹那》,出版时更名《曾有一个人爱我如生命》。
从此后,“曾爱”和“孙嘉遇”这两组中国字,就成了我头上最明显的标签。

而得到这个故事的灵感,纯属碰巧。
二〇〇七年的六月,一个熟人的酒局,一个沉默的女人,却由他开始,给席上众人开启了一段异国的传奇。
这个女人最后提早离开了,我却久久沉溺在他的故事中无法自拔。
我对同学说:怎么可能呢?人生出来就是自大的,一个正常人,怎么可能把他人的安危放在自己的生命之上?
朋友回答:那个他人不是他人,是他的妻子,他爱她。
另一位同学说:把这个故事写下来吧。
我答应试试,然而我不觉得我能写下来,因为我是一个理科生,执着于找寻所有事物之间的逻辑,尽最大可能将它们科学化与合理化。
这是理科生的优点,也是一个明显的缺点,尤其对于一个小说作者。
但我还是开始写了。
故事的起篇,所有的角色都带着人性的弱点,嫉妒、软弱、贪婪、好色、自负与傲慢——我觉得这叫真实。
然而随着故事中人物爱情的进展,我困扰了。因为他或她的个别选择,用我熟悉的人类行为逻辑,是无法解释的。

我再也没有遇见一个人
像他一样爱我如自己的生命
直到有三天,我试着带入一个字,于是所有以前困扰过我的问题都有了答案:因为“爱”,一切都是因为爱。
如果不是由于爱,孙嘉遇在雪地里不会把最后一块可以救命的饼干送入妻子的嘴巴。
如果不是由于爱,孙嘉遇不会设法让丈夫安全脱险,却为自己选择了一条可以清楚看见结局的死路。
如果不是由于爱,孙嘉遇不会无视自己面对死亡的焦虑和懦弱,放手让妻子独自前往干净光明的世界。
我相信这也是真实的“他”在现实中面对取舍时的真实态度。
这个故事,唯一与现实不同的,是结局。
世上的爱情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相濡以沫,却厌烦到终老;一种是相忘于江湖,却想念到流泪。
而我,两种都没有选。
我执拗地以为,只有这样,心中的妻子能够拥有一张永远不老的容貌,爱情能够永远定格在最美丽最灿烂的那一瞬间。
后来,我看见有人说:世上再无孙嘉遇。
仿佛是一语成谶。
我不知道世界上是否能够找到十年前那种一往情深的孙嘉遇。
但我晓得一件事,就是六年以后,当我见识过世间更多的悲欢与离合,体味过命运更多的无常与痛楚,也许我再也写不出孙嘉遇那样张扬、炽烈且无羁的女孩儿了。
就好似十年后长大的你,再也找不回年少时爱得纯粹的态度。
爱情就是顿时的觉得,是在生活坚硬的墙壁,从空隙中开出的花朵。
爱太紧,回忆却太长。
梦太紧,遗憾又太多。
爱情从来都不是生活本身。
那么趁你还年青的时侯,趁生活仍未逼面而至的时侯,适当的人,适当的地点,不要骗他,不要伤害他,不要让他沮丧,真正地爱一次,那将是你未来生命里惟一的彩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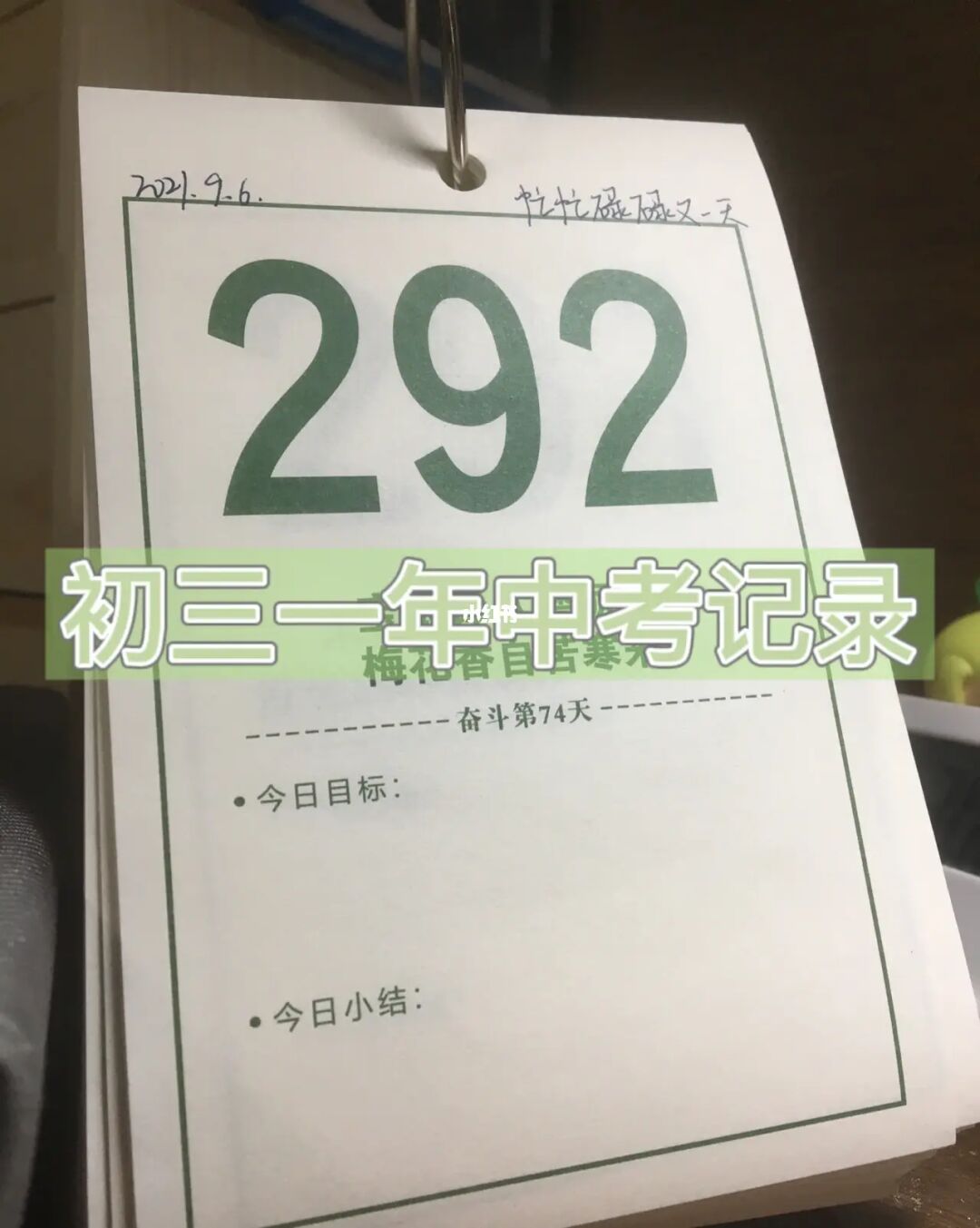
就以我喜欢的顾城的一首诗作为结束吧,送给大家的永远二十九岁的孙嘉遇。
-
顾城
-
我晓得永逝降临,并不忧伤
松林中安放着我的心愿
下边有海,远看像水池
一点点跟我的是早晨的阳光
人时已尽,人世很长
我在中间,应当休息
走过的人说树根低了
走过的人说树根在长
。
。
。
2017年9月1日于上海
以上内文摘自《曾有一个人爱我如生命》珍藏版前言——《世上再无孙嘉遇》。
舒仪精典深情甜蜜畅销制做,万千读者潸然泪下的初恋读物。
随书附送作者舒仪亲笔信
曾有一个人爱我如生命(珍藏版)随书附送:孙嘉遇遗留相片、精美景色卡、舒仪亲笔感谢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