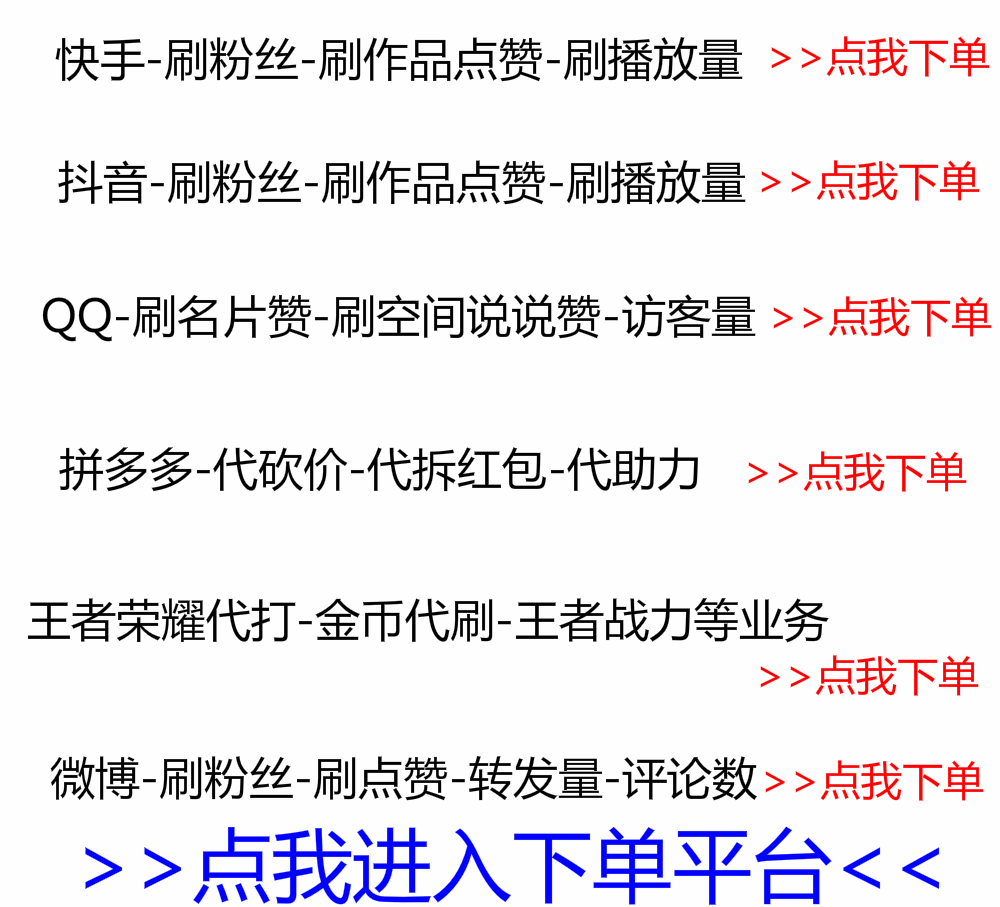
《我在现场》系列之(四)(本系列往期文章,请见文末链接)
所谓的世事洞察、人情练达不是老于世故而是擅长生活尤其是擅于感受生活
——杜鹃
文 | 杜鹃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
在研究生学习开始之前,我是一个不仅旅游从来没有出过南京,除了念书从来没有其他经历的北京女孩,家教甚严,背景简单。好在生在底层,有个大家庭,街头巷尾的三教九流也算见过一些。可是真正的生活阅历,可以说是少得可怜。我除了没怎样出过这个城市,确切地说上学院之前,我都没怎样出过家和中学之间的那几条街。一个人坐公交车超过10公里,那都是15岁以后的事儿。帝都的热闹繁华,似乎也和我这个不谙世事的学生妹没哪些关系。
也许,越是隔绝的儿子就越渴求自由,越是家教严就越会出格反叛的缘故吧,对于自身的沉痛恐惧,对于这个社会的热切盼望,充斥着我的痛苦青春。这时《北京青年报》上的一篇文章,让我晓得了人大有一位研究“性”的麻辣院士——潘绥铭。
在哪个相对闭塞的时代,我想办法弄到了他写的《性的社会史》,然后裹了好几层有欺骗性的封套以后,在被窝里,利用中学时代宝贵的睡眠岁月读完了它。多少年来,对于性的懵懵懂懂,遮遮掩掩,在这本书的启蒙下如拨云见日,如醍醐灌顶。我对那位传说中耳朵硕大的院士的崇敬油然而生,以至于多年后拜在潘门派下,我还忍不住称赞他的睿智诙谐,不顾马屁山响之嫌。
然而,真正从事性的研究并不是这么一帆风顺。第一次鼓起勇气提出要研究性,是在中考之前。由于受了那本《性的社会史》的“蛊惑”,我在报志愿之前,正式跟我母亲提出我要学性学!我妈当初真是淡定啊,居然没有当即就断然拒绝我,而是在第二天才胸有成竹地跟我说:“我己经问过了,根本就没有如此一个学科。”
这可让我傻了眼,分明是报纸上介绍的,人大有这样一个性学院士啊,怎么会没有如此一个学科?一头雾水的我翻了半天《报考指南》,还真是没有这个专业。就这样我的第一次“越轨”之举破产了。当年网路没有如今发达,我的环境又相对闭塞,我像好多小学生一样根本不太晓得这个“学”、那个“学”到底是学哪些的,哪里晓得那位我钦佩的性学院士,其实是在社会学系工作呢?
大学时代,终于逃脱了家庭的“牢笼”。我第一次在人大看到了潘老师的课,简直重新燃起了我想要研究性的冲动,于是我借助考研的机会又一次做出了选择。但是这一次我其实比原先聪明多了,没有跟家里人说我要研究的是性学,只是说要学婚姻家庭社会学。可怕的是,人扯一个谎真是要十个谎来圆,以至于到现今为止,我的真正所学,在家人的眼中仍然是婚姻家庭社会学,这样一个温情而无伤害的,且适宜女孩子的专业。当然,这毫无疑问是我双重人生中比较低迷的一幕。
在性研究的路上摸爬滚打这几年,调查成了家常便饭,“小姐”、吸毒者、艾滋病感染者……那些被恐吓与被损害的人们,一次次成为我的采访对象。他们的经历和故事,丰富着我仅有的社会阅历,丰富着我对生活的理解和感受。
目录
01.调查不是一问一答
02.旁听出真知

03.调查是沉溺于生活之中,理解生活 04.“你问了这么多,能不能跟我来一次?” 05.活法
调查不是一问一答
通常,我们的“红灯区”调查会通过引路人举荐,在某个场所植根,对这个场所的“小姐”、“妈咪”、客人以及其他相关人进行观察、访谈;在同吃、同住、不同劳动的过程中搜集资料。在参与过小型的问卷调查和形形色色的面对面采访、焦点组采访过后,一个研究者会特别享受这样一种完全不同的田野经历。一次在中国西部一个省会城市的调查中,我阴差阳错地把我的调查地点挪到了一间“红灯区”中的理发店里,在这儿有幸经历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田野调查。
在很多人的眼里,“红灯区”中的理发店就是亮着红灯,里面没有任何理发工具的洗脸房,可是我所选择的这家是名副其实的理发店,是“小姐”们日常修剪毛发、打理造型的地方。这里是“小姐”们的公共空间。她们聚在这儿聊天、休闲,既没有工作场合中的职业老道,又不是私人场合里的真情流露。我作为一个旁观者,一个参与者,在这儿见识到的是生活中硬生生的“小姐”、社交中的“小姐”、女人圈中的男人。
理发店的老板娘李姐,是个30多岁的男人,中等身材,偏胖,皮肤白净,典型的西北人样貌。因为在步入这个“红灯区”的时侯,我们和此地“看场子”的人打过招呼,确切地说是喝过酒(就是这个故事让我获得了“喝倒大队”的美名,现在想想真不是酒量了得,而是不知深浅)。因为饭桌上的良好表现,我们很快获得了她们的信任,同时也是经她们举荐,我很顺利地在李姐的理发店里安顿了出来。
李姐中学结业以后,学了三年美容美发,毕业后在家上面帮忙做粮油生意。后来她家的店被占了,就地盖起了一个大庭院,里面所有的房屋都堵死上了窗子。她们当时还很吃惊,“这是要干哪些啊?房子都给变成这样了”。后来就看这小院上面来了好多小姑娘,个个都爱装扮。这个时侯她才想到,自己当初学过美容美发,要是在这小院附近开个理发馆肯定人多,于是在“红灯区”里面的理发生意即使开业了。
此后,李姐在这上面做了10年。其间,她结了婚,生了儿子,死了父亲(弟弟的事情是我临别的那三天她才告诉我的)。关于李姐的故事,我们最后再讲,先谈谈在这个奇特的公共空间里,我认识的人和发生的事。
在这个“红灯区”里,很多“小姐”在复工前就会到李姐这儿彩妆、做眉毛。她们在这儿聊天、打扮,进来的时侯是睡眼惺忪的小姑娘,出去时是清纯娇俏的“小姐”。在这个过程里看见、看到的好多信息,在一对一采访中是很难得到的。一般来说,访谈如同一个人造的情境,目的是得到信息,双方会身陷一问一答的节奏中,访谈者害怕忘词,被访者害怕叙述危机。而且更容易被研究者效应影响,给出所谓的“正确答案”。而在真实社区中的田野调查,信息搜集的过程则愈发灵活、更有张力,当然也须要研究者更有耐心、更加敏锐。
下面是我在李姐理发店里蹲点时的一段采访记录,源于我们课题想要了解的中心问题之一——“小姐”如何建构“脏”的概念。
下午的时侯,我问齐文“你认为哪些是脏?”她说:“对我来说好多东西都可难受了。”
我继续问她:“那具体有哪些呢?”她憋了半天没说出来,后来忽然跟我说:“我认为在外边沾花惹草的女人就是脏!”
我问她:“那你每晚接触的女人,岂不是好多都是这样的?”她想了想,说:“也是啊,反正我就感觉她们脏!”这段对话就此告一段落。
后来聊天中,她无意中又说到如此一个事情:“我们家有两个‘小姐’就给顾客做口活,那个就非常难受。有一次我们在酒吧喝水,那两个女性过来了,要一起吃!我们放下牙签就走了。”
这并不是她回答我问题的时侯说的话,而是我们在聊天过程中谈论口交的时侯说到的。显然,日常对话中的信息,比他们刻意回答问题时侯要真实、生动得多。这并不是他们故意隐瞒,而是由于他们平常根本没有想过我们所问的问题,你一问,她才开始想,因此很难全面回答。可是,她们会很可爱地记住你的问题,也许由于不满意自己给你的答案,也许由于从没认真想过你的问题,所以当他们突然想到一个挺好的答案时,就会迫不及待地告诉你。

这种情况在观念调查时尤其常见。被访者在短时间内给出的回答,经常不能概括她们的真实所想。结果,在一次性的面对面采访中,我们带回去的,其实只是一个半成品的回答。只有田野调查才有机会帮我们得到愈发深入、有血有肉的答案。
比如在了解“小姐”对于“健康”的认识的时侯,我常常遇见的情况是,她们会停下来想一下,然后给出一个例如“健康就是没有病”、“健康就是将生命延长”、“健康就是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大脑健康”这样的回答。这些毫无疑问就是对健康概念的第一反应,但这样的回答常常模棱两可甚至是敷衍了事。可是在田野调查中,很多不期而遇的风波,会加深调查双方对问题的理解。比如下边的一个情形:
下午,李姐的店里发生了一个小小的骚动。本来一帮女性在一起谈论面包车,大家都对保时捷、大奔称赞有加。说起了一辆你们都认识的迈巴赫敞篷街车,经常到这儿来,丹丹在一旁说,她认识那种人,有时候会在一起玩。大家谁都没说什么。谁料无巧不成书,说话间那女人的电话就打过来了,说要来接她。不一会儿的工夫,车就到了李姐理发店门口。虽然不是大家说的那辆敞篷街车,但也是辆宝马货车,而且很新。男人进来找丹丹,他看起来三十五六岁的样子,中等身材,穿着一件带毛衣领的黄色夹克、黑皮鞋、黑裤子,一身黑,看着挺干净、挺讲求。他跟丹丹说了两句话就把她带了出去。
看得出来,大家很惊讶,只是谁都没有在言语中表现下来。当时丹丹还没有化好妆,所以面包车在庭院上面兜了一圈,调了个头就回去了。回来后,丹丹赶快让李姐帮她弄毛发化装。此时边上的女人们耳朵里放射着妒忌、好奇、轻蔑等各类光芒,只是谁也没有在话语中表现下来。
丹丹她平常都是很高调的人,可是今天下午她也很开心。看得出来,那个开奥迪的话题人物拉她出去兜风,让她感觉十分有面子。正在丹丹春风得意的时侯,有一个平常不是常常来的男人打破了店里奇特的氛围,问道:“哎,你说那男的穿的那衣裳的领口,是真貂的么?看着不怎样像啊?要是真貂的,一薅才能薅下来,真皮草不会皮屑的。下回你薅一个瞧瞧。”
说完这话,大家无一人应和。这男人走以后,丹丹把她臭骂了一顿,转过头来跟我说:“你看,你不是问健康吗?我告诉你,这就叫心理不健康!”在前面的几天里,这真的成了心理不健康的一个反例,旁观了这件事的很多人就会提及。后来我发觉,很多“小姐”对心理不健康的定义,其实就是“气人有,笑人无”。
生活,总是比我们想像的愈发丰富,比语言更丰富。可是一对一采访中的提问,却常常是围绕着深思熟虑的采访提纲展开的,我们一般迫切地想获取我们觉得有价值的信息,而这些迫切在采访中常常会带来信息的损失、双方的沮丧、误解甚至诱导。只有当我们深入田野的时侯,这种时间的狭小和对信息的矫饰追求才能渐渐淡化,才能促使调查显得这么丰富而有张力。
旁听出真知
这是我从一位出租车司机口中看到的话:“但凡哪些事儿你想知道,你不能问,你得听,还得偷听。”这话,我深以为然。
实际调查中的好多事儿是不便捷问的,比如涉及个别违法行为,或者非常私密的情况。即便你问了,对方也可能不会给你真实答案,遇到这些情况就要留意听。如果说偷听有违研究伦理的话,那么旁听则是得到真知的一条捷径,研究者所须要做的,就是有足够的耐心和敏感。
在“红灯区”里,吸毒其实是公开的秘密,但是假如直接问的话,也不一定能有人回答。我在刚才到的时侯,就冒冒失失地问了其中一个“小姐”吸毒的问题,但是人家很巧妙地回避了,直到几天以后的一个晚上,答案才出炉。
一天夜里快放学的时侯,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过来,管李姐借锡纸(我当时并不晓得是干哪些用的,也没有多嘴问)。李姐说没有,就把他打发走了。后来,屋上面的几个女性就议论开了。丹丹说:“理发馆用的锡纸太厚,不好溜。”其他人也表示同意,我这才明白过来,她们在说“溜冰”的事情。话题打开后,几个人就开始说自己“溜冰”、嗑摇头丸的经历。原来这几个人都是溜过冰的,其中也包括先前没有回答我问题的那种小姑娘。
旁听,有时还可以帮你把听来的和采访来的信息进行互证。这些信息甚至可以帮你辨识你所搜集到的资料的真实性,也可以帮你判定是什么情景诱因在起作用。
比如在关注“小姐”的职业安全问题时,我常常看到人们议论一个姓杜的女孩怎么怎么坏,李姐也总说:“她常常从中学上面骗这些小姑娘下来,还骗顾客开处的钱,可坏了!她还由于骗顾客的钱,被人打过。”我见过这个女孩,她为人挺冷的,不爱理睬人,也亲眼见过她背上有很大的一块疤。直到后来,我在李姐店里待得时间长了,她才时常和我说话。

杜姓“小姐”告诉我:“我在中学里的时侯,就带人下来干(这和李姐告诉我的很吻合)。后来我感觉没意思,就不干了。去北京学了半年美甲,在那边没做‘小姐’这行。后来又去了上海,还是学美甲,可是那行太麻烦了,我干不了,就想还干回这行,但是要带人下来,这样就能挣更多钱。结果让人家给骗了!”
原来是,有个人让她找两个女孩去北京,“说让我抽他们的台费,我不用陪酒。结果,到了那就让我陪酒。我死活不做,就打我,拿滚水烫我。后来我找同学替我把医药费打过来,才回去的。”
在这个事例里,猛一看,李姐提供的部份信息和被访者的纳差确实比较吻合,但是少了一些细节,而且似乎带着对她很大的隔阂。现在我才晓得,这位“小姐”同样遭到过侵犯,同样是受害者。
可是杜姓“小姐”所说的话,同样存在疑虑,比如为何从前离开这行后又重操旧业?如果在中学时就投身这行的话,真的会为了拒绝陪酒而被打么?到底是因为不愿卖淫,还是由于李姐他们所说的欺瞒顾客?当然在这个事例里,非常遗憾的是,到最后我都没有弄清楚,到底是什么诱因引起她遭到侵犯。如果我们的研究是关于“小姐”被害的,那么这毫无疑问须要进一步考量,可能须要愈发深入的采访或则更多方面的信息。或许我们永远也不晓得所谓的“事实真相”到底是什么,因为人们总是有办法隐瞒一些事情,甚至改写自己的记忆。
但是我们至少能得到对方想让我们晓得的东西。事实上,除此之外,我们又能晓得哪些呢?所有的调查莫非不都是这样么?
调查是沉溺于生活之中,理解生活
还有一个故事是关于李姐的。
李姐除了是在“红灯区”里做正经理发生意的老板娘,还是一个厉害的角色。在我离开前的最后三天,我们的关系己经非常好了,她带着她的儿子请我们喝水,陪我遛弯买当地特产,跟我聊他父亲的学习,俨然把我当成了同事。事实上我们两个的确保持着联系,离开后的几年里,我们时常会打打电话。她会问我在广州买房、学美容美发、看病等好多问题,并且经常约请我们一家回来找她玩。
在最后三天,李姐给我讲了很多她自己的故事,包括她拉着在事故中丧生的儿子的遗体找肇事者追债的经历,让我更加意识到这个男人不简单。李姐真是不简单,她的店只有她一个人,她既是老板娘,又是理发师、美容师,还是小工。她似乎从不涉及“性产业”,但是在这个产业链中,她是靠“小姐”生活的人。她和她的店如同一张蜘蛛网,网罗着这个相对封闭的“红灯区”里的各类关系。当然,作为编织这张网的人,她和网上的每个人都有挺好的私人关系。
在她的店里,有很多常客都和李姐关系密切,有些女孩甚至管她叫姑妈。在我的观察中,李姐对他们也挺好,非常关心他们,经常像姐姐一样教育那些小姑娘;有时也会收养一两个关系好的,晚上在她店里居住。李姐很多次跟我慨叹,说这种小姑娘很可怜,很苦,经常被人欺侮,被这些小后生骗。她说:“这些小女孩,其实多数心都挺好的,没有害人的心。”
但是有一次,她陪我去买特产的时侯,我们在车上聊天,说起这种小姑娘们的时侯,她忽然说了这样一句话:“婊子无情,贼无义,你和他们相处不能太实心。”这和我平常印象中的李姐差异简直太大了。虽然,同情“小姐”和用“婊子”这样的词来尊称他们并不矛盾,但是这和我往年对于李姐对“小姐”态度的判定也有很大差别。震惊之余,我开始反省,李姐往年怜悯“小姐”的言论都是在她店里说的,而说“婊子无情,贼无义”的时侯,却只有我们两个。我相信,这两种心态对她来说都是真实的,只是情景变了,或者说,没有哪种说法是真实的,都是在不同场合的操演。
理发店里的她,是“性产业”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小姐”是她的客人,是她的同学,是她的衣食父母。她在“红灯区”里做了这么多年的生意,耳濡目染着那儿来来往往的男人的喜怒哀乐,同为女性,自生怜悯。但是她其实不是“小姐”或者“妈咪”,只是与这个行当伴生的一个服务行业从业者。她的一句“婊子”,一则带出根深蒂固的对“小姐”的戏谑;二则为了与我攀谈时和“小姐”划清界线。在她看来,我是和她近似的人,所以她更多地和我聊丈夫、聊小孩、聊生活,和我保持的是另一种男人之间的友谊,所以在和我独处的时侯,她就会说出那样一句话来。
这正是田野调查的魅力所在。它不是简单的一问一答,也不仅仅是听锣听声,听话听音;而是在情景中理解人,是沉溺于生活世界之中去理解生活。
当社会科学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所谓的定性方式来进行研究的时侯,人们虽然更喜欢把采访当成定性研究的惟一方式,而且仅仅是搜集无法量化的文字资料,然后把采访记录化约成可量化的方式,进而去寻求个别固定的模式以总结和概括错综复杂的生活。结果,定性方式所指出的情景,就被吞没在“被刻意捞上来的”访谈记录当中了。
其实,情境性也是最朴素的生活道理,所谓“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是也。这不是“表里不一”,而是生活策略和人生常态。如果我们没有在田野调查中,获得对生活世界复杂性的充分认识和理解,没有发觉和总结生活情景的多变性,仅仅借助单一的采访,那么,这些脱离了具体情景的记录文字,还有什么意义吗?恐怕定性研究的魅力也就不复存在了。
“你问了这么多,能不能跟我来一次?”
第一次进行男客的采访就让人印象深刻,因为我们往年的研究中都以研究“小姐”为主,一直没有找到太好的研究男客的方式。借着一次艾滋病课题的问卷调查,我们准备尝试着接触一些男客。这样的采访设计,起初让我十分苦恼,当时我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看起来稚嫩青涩,让我去采访“嫖客”,害羞、害怕、紧张、兴奋各类情绪五味杂陈,而且第一个采访对象就让我终身难忘。
他是一个卖石子水泥的小老板。他的店铺很小,十分破旧。小店位于的那条路正要拓宽,这家破破烂烂的店铺和边上所有等待回迁的房屋一样,看起来岌岌可危。头次见他,他就躺在自已小店的床上,当时是夏季,还铺着草席,被子没有叠,团在一边,床脚下就是电视,我进去时正在放着一部日本恐怖片。
那一次并不晓得他以前找过“小姐”,只是为了做一份问卷。因为他毫不忌讳地在是否找过“小姐”的问题上给出了肯定回答,所以我有意多交谈了两句。他很是配合,并且留下了联系方法。
时隔两个月以后再去,他早已换了地方。我发短信跟他联系,他说他早已迁往离红庙不远的大井去了。我根据他的描述,很容易找到他的新门店。说是门面,这里比第一个地方更像是一个民宅,里面没有任何货物,只有一张床和一个电视,地上摆着几个饮料杯子,拖鞋斜靠着一个杯子倒着。他还是老坐姿,斜靠在床上,脚下是成一团的毛毯。
我一进门,尽可能地表现得很热络,问他:“你丈夫呢?”“她回去了,十一前就回来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去。”
他这样回答,我挺惊诧的。他这个女朋友,是第一个跟他住在一起的人,当时他还是处男,但对方早已不是第一次了。他们俩在一起许久了,如果没有闹分手,两个人不会连对方什么时候回去都不知道。于是就问他,打算什么时候离婚。他说,不知道呢,两个人都想瞧瞧,再决定什么时候离婚。他说,他们这叫“试婚”。我很好奇,问他这个名词是哪些时侯晓得的。他说就是前两年,一起下来的年轻人都这么说。
据他说,从故乡下来的年轻人,都会试婚,但是和试婚对象最后登记的不多。这种试婚的情况到二十五六岁都会结束,年轻人带着“老婆”和早已降生的第一个女儿回去登记、结婚。这样生了儿子再回家结婚,据说是因为想多要一个女儿,然后决定给那个上户籍,以便隐瞒一个或则交些罚金。
在此次采访中,他对所有问题都十分配合,回答很是谦虚,这让我感觉一切比想像中容易多了。访谈进行得很顺利,直到他跟我提了一个问题:“你问了这么多,你能不能跟我来一次?”
我当时就吃惊了,心跳加速,面红耳赤,不知所措。我头脑里第一反应是夺门而出,好在他的门仍然开着,离大马路有着不太远的一段距离。可是我又一转念,不能就这样落荒而逃啊,太不专业了,好像自已很胆小,动真格的就不敢谈了似的。
不知道当时究竟是什么动力让我留了出来,只是觉得他不会把我怎么样,于是我断然跟他说:“不成。”现在回想上去,好天真啊。如果对方真有恶念,又岂是我一句“不成”就能拒绝得了的呢?好在他也只是试探性地问了一下,我说了不成,他也没有霸王硬上弓。看形势还好,我竟然又继续问了几个没有完成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他又表示了几次他的看法,直到我提出采访结束,要给他采访费,才战战兢兢地离开了他的店铺。走的时侯我还强作镇定,但几乎没敢回头看,怕别人追上来,把我拖回那间小平房先奸后杀。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后怕,自已当时如何敢一个人去做采访,怎么敢意识到危险还不赶快结束?
多年以后,回想起这件事,当初的焦虑和后怕己经不再这么鲜明了,取而代之的是反省。经过这么多年的社会调查和采访,有些理念己经深入我心,比如这样一句话“调查就是求人办事”。在我此次险些“失身”的经历里,那个小老板的话很值得玩味:“你问了这么多,你能不能跟我来一次?”细想起来,这话的意思好多:你都问了这么多了,我都告诉你了,你能不能跟我来一次?作为交换?作为回报?如今想想,这也许是挺正常的事情,只是我当时给他扣上个色鬼强奸犯的围巾,再加上无知少女的被迫害妄想,才会吓得自己失魂落魄。
作为调查者,我们主动拿着问卷,拿着提纲甚至拿着录音笔,去问许多人家根本不关心的问题;人家耗费时间、精力和耐心,去满足你的研究热情,难道只是为了那一点点礼品或则采访费?我们其实希望这种小恩小惠可以作为补偿,但是当我们自己无情地拒绝别人的访问要求时才会晓得,那些小东西是很难成为他人接受访问的理由的。

因此,对方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就真真是对我们极大的耐心和帮助了。当然,这里有些人是贪恋小恩小惠,有些人是好事之徒,有些人只是为了消磨时间或是满足好奇心;但无论如何,他们耗费了自己宝贵的时间,分享了自己隐私的经历和看法。就为那些,我丝毫不能责备曾经那种提出要跟我上床的水泥店老总。试想,一个满大道找人谈性的女孩,会让女人形成哪些看法呢?我主动找上门来,让他谈出他这些隐私的经历和看法,他跟我要求上个床,也实在不过份。况且他只是要求而非逼迫,这样想起来,他还是相当绅士的。
说到底,这样的遭到,其实只不过是一个调查者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是至少的伦理原则,是最低限度的互利。我们没有道理认为我们的研究目的有多么高尚,研究动机有多么的单纯。所有所谓高尚单纯的动机,都要落实到研究中,进入被访者的生活世界里,而且被对方所理解,那才是真实存在的。这如同好多“小姐”永远觉得我们是来踩点的,自己早晚也要颁布;就像那位小老板八成觉得,既然我可以如此轻率地谈性,那也就一定可以随意地射精一样。我的访谈者很慷慨地跟我分享了他的人生经历,而他希望我能跟他分享我的身体,这或许可以理解,只是不能接受而己。
当然我承认,在这个风波里我是辛运的,的确不是所有情形都可以这样驾驭。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中,访谈者可能碰到人身伤害的恐吓,遇到财产安全被侵害,遇到羞辱以至咒骂。但是这种侵犯的前提是,我们的研究行为首先就进犯了他人的生活。如果人家接受,那就是纯粹的帮忙;如果不接受,也是理所应该。因此,除非对方用特别不友好甚至敌意的形式拒绝你,否则,就请你安静地走开,同时在适当的时侯保护好自己。
请初学者不要像我一样莽撞,因为不是每位被访者都有着这位小老板的自制。更重要的是,请初学者一定要态度平和并保持敏感,因为每一个被你敲开的门背后,都有他自己的世界和故事;想要听,不是只带一副眼睛就可以;想要听,请放下你的衡量和偏见;想要听,你还要随时打算讲出你自己的故事,准备有限度地分享自己的秘密。那么,底线在那里?这就看你的判断力、勇气和诚心了。
活法
在博士结业的谢师宴上,我喝多了。在潘老师门下这几年的东奔西走,仿佛历历在目,一朝结业,居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觉得。
泪水和着泪水的我,当时最大的感慨之一就是:再也不用做调查了!再也不用带着一帮本科生,在陌生城市的火车站广场上,彷徨着住那个酒店了;再也不用为了节约住宿费用,住在大学城里挂着带血帐子的招待所了;再也不用为了让某个街道校长配合我们的调查而点头哈腰了;再也不用为了才能步入现场,和余孽们喝得几乎酒精中毒了;再也不用在炎热的夏季,辗转于武汉各大建材市场找寻采访对象了;再也不用在个体户中调查“性”而随时被人想入非非了;再也不用由于调查的问题太敏感而被阿姨破口大骂了;再也不用在“红灯区”被人当作“小姐”往包间里拉了……
现在,几年过去了,当初再也不想发生的事情,果然再没发生过。我的生活也进入了房屋、车子、孩子的白窠,住在上海这个我并不真正熟悉的家乡,过着安定的生活。可是,总认为缺了点哪些:那种实实在在的活着的觉得,越来越不清晰了。
原来,这些年来我们就是在用调查的方法,接触和认识他人的人生、别人的活法。这上面有很多是我们往年所不理解的,主流社会所不接受的活法。但是有很多人就在用这些方法活着,而作为研究者,就是要理解这种不同的活法,理解它们的实践的合理性,搭起私人经历和社会背景的理解桥梁,填埋不同个体经验的解释鸿沟,这或许就是所谓的世事洞察,人情练达。它不是老于世故,而是擅长生活,尤其是擅于感受生活。
经历过那些,你的心里肯定会留下一片永远憧憬的田野。
* 本文与若干作者的性社会学田野笔记一起收录在《我在现场——性社会学调查手记》一书中。
本书开放下载地址:
本系列往期文章
性研究ing你想要的性研究都在这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