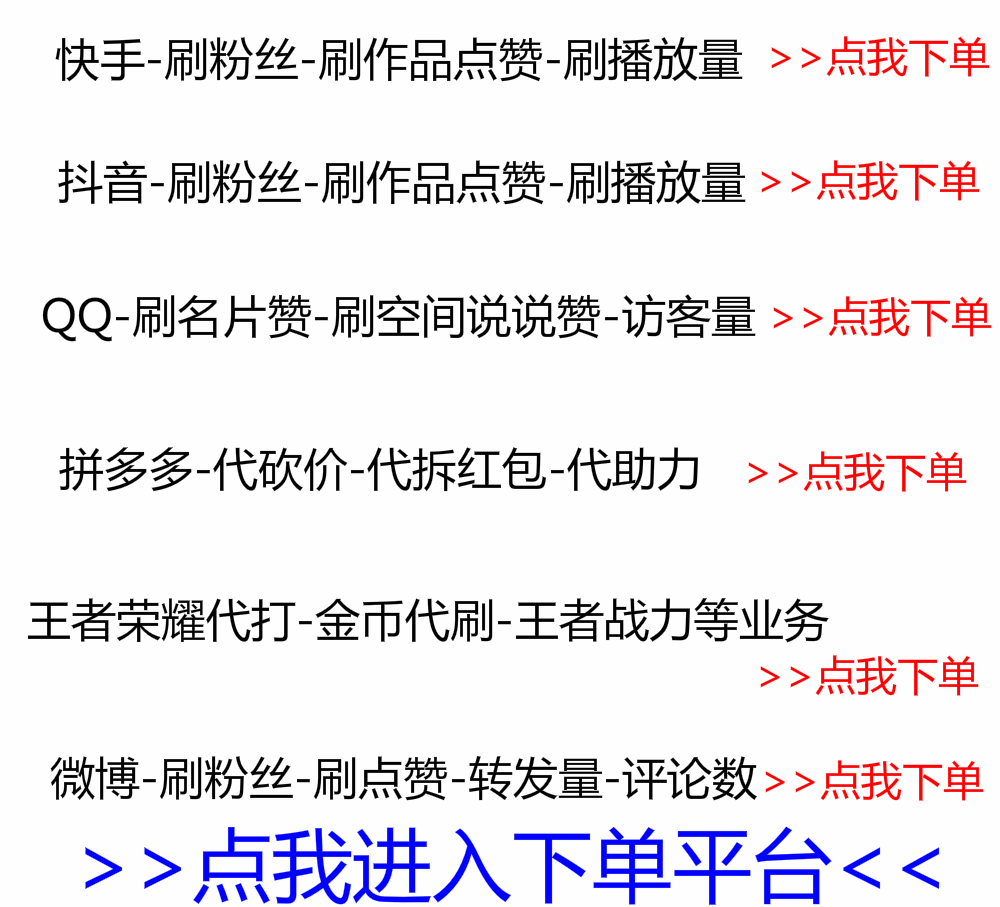
阅读前请点击上方蓝色字体“晶心雅”,再点击“关注”,即可免费领取文章。完全免费订阅,请放心关注
一样。这时候他可以找支烟抽起来,借点热量。黄昏来临,屋内的东西只剩下一些轮廓。暂时懒得开灯了。我也可以点一支烟,看着烟头上的火光闪烁,像是亲密的耳语,只有我能听见。如果你生气了,你还不如发泄你的怒火,吸他十几次。有客人来了,累得说不出话来,或者说不出话来,何不赶紧坐下呢?这个时候最好拿起一根烟捂住嘴等对面的人。如果他也这样做,他会尽力在烟雾中爬行。每个人都有一个新伙伴,可以在附近闲逛一段时间。
我以前吸水烟和干烟,但这是一种无害的爱好,但现在吸烟已成为一种风格。烟卷的手指是黄色的,放下吧。用烟嘴,不仅麻烦,而且小气,而且离香烟那么远。今天外衣破了个洞,明天马甲破了个洞,放过他吧。香烟中的尼古丁可以毒死一只小麻雀,然后放手。总之,跛脚的麻花其实还是“无动于衷”的。香烟有好有坏,口味有浓有淡,能分辨口味的就是专家,选择抽的就是大方之家。十年前,我写诗;然后我停止写诗,写散文;人到中年以后,散文不能写太多了——现在比散文还“散”。很多人苦于无话可说,也有很多人苦于无话可说;他们的痛苦还在话语中,而我无话可说的痛苦却在话语之外。在这个大时代,我感觉自己就像一片枯叶,一张烂纸。
有人说我的“铭记之路”是“平如山脊”“笔直如箭”;我从未有过激动人心的生活,即使是在我年轻时别人想来的时候。我的颜色总是灰色的。我的职业是三位老师;我的朋友总是少数,而我的女人总是少数。有些人的生活太丰富太复杂,忘记了自己,看不清自己。我一直都知道并记得我是多么的简单。
但是为什么要写诗呢? ——虽然都是废话。这就是时代的目的!十年前是五四运动时期,大家精神抖擞,朝气蓬勃,逼迫着我这个小学生,于是我就跟着别人的脚步,谈自然、谈人生。但这些只是类别。说句公道话,我是个懒惰的人,从来没有经历过什么大逆境;不去琢磨,也不去体验,品类终于只是品类,这里只是廉价,感伤新瓶旧酒。那个时候,芝麻黄豆的大事就被庄严地写出来了。现在看,只是苦笑。
先驱们告诉我们说他们的话。不幸的是,这些自我往往很简单,他们所说的就是他们所说的;他们终于厌倦了听他们说的话。 - 我是他们中的一员。这些人自己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只是说出了中外先贤所说的,世界青年会说的话。只有少数人真正有自己的话要说;因为只有少数人真正过着和品味过那种生活。普通人只是在不同程度上像往常一样生活。
这个简单的意思还是要到中年才明白;十几岁的时候,我有点热,但我没有想到。中年人再糟糕,也希望能看得清楚、开诚布公。此时,我的面前没有雾,上面没有云,只有我自己的路。背负着经验的重担,他一步步踏上这条无尽而真实的道路。回头看看年轻人的情绪,心里顿时松了口气。他愿意分析他背上的经历,而不仅仅是他年轻时的经历;他不想远远地揣摩它,而是把它剥开来看。他也知道,撕下来之后,弹跳力就没有了,但他并不在意,他知道,冷静里有他需要的东西。如果他在这个时候偶然说话,绝不会是感伤或印象主义,他会告诉你如何走他的路,否则,剥去什么。但是中年人很胆小;他越来越听别人的话,说的不说,说的也不好说。所以最后往往无话可说——尤其是像我这样的普通人。但是沉默对于常人来说是很尴尬的,我说痛苦是无以言表的。
如果一个中年人还在弹年轻人的曲子,曲子好坏无所谓——这不是一个坏主意,但总感觉“像一件严肃的事情”。他会用巨大的力量写出热气腾腾或含泪的文字;一个神经敏感的人,无论是在自己身上还是在别人身上,都不能轻易地承受这一切。这就好比老太婆和小姐姐们当众抹黑炫耀,没必要。
其实这一切都可以说是无稽之谈,想想我们的年龄吧。这些天,我要的是一个“代言人”,凡是说话的人都被视为“代言人”;他们根本不在乎自己的话。这样一来,像我这样的人,过去的嚣张之罪就可以解脱了,现在无话可说。
但最近,在戴的《唯物史观文学论》的翻译中,我看到法语中的“没什么好说的”实际上与“一切都好”是一致的。呜呼,对我来说,对我的年龄来说,这是多么可耻的一句话!罗马(Rome)是历史上伟大帝国的首都,想象中的它总是一千零一个。虽然它的辉煌早已过去,但从散落的废墟中,后裔依旧可以看起来像是一百零一个。这些遗址,无论是旧的还是新发掘的,几乎随处可见,仿佛是刻意装饰古城的。这里几根石柱,那边几道残垣断壁,承载着往日的尘埃,孤零零地在坑里;夏日正午的阳光虽然照在上面微弱,但并没有多少能量。罗马最大的市场。这是古罗马城市的中心,有宫廷、寺庙和住宅的遗迹。 Castor和Poros神庙的三根科林斯式柱子由顶部的一块石头连接起来;他们是全场最帅的,就像三个妖艳的少年用手捂着额头,看着这里。一个古老的市场。不知道有多少人整天挤在这里,各有各的心思和方法;现在只有三两个游客在死一般的寂静中指指点点。拐角处有一所房子,状况良好;一侧是三间屋子,壁画模糊,地面镶嵌石块;隔壁的房间是餐厅,壁画很精致,画的都是立体的题材。这对餐厅来说非常重要。市场上方是帕拉蒂尼山,这是一个经历过风风雨雨的地方。起初是一个只有茅草屋的村庄;罗马共和国末期,这里住着一个贵族家庭;到了帝王时代,更是繁华。
游人上山,两旁雄伟的房屋还留有完整的黄土空白,尽显当时豪门的气息。屋顶为平地,原为多园,总称法内斯园,也是四百年前的旧址;现在花草树木装饰,一角有一个小喷泉。望着这花园脚下的古市集,尽收眼底。市场的东边是斗狮场,大致大小可以看到;在众多宏伟的遗迹之中,这是最好的情况。外墙是一个大圆圈,分为四层,必须抬头才能看到顶部。下三层都是同色的圆拱和柱子,上层只有小长方形的窗户和屋脊。这种简单的对比,让人觉得这座建筑是一个整体,就像直通天穹的松柏,古老的枯亭,没有多余的细节。里面的中间原本是一大片平地;中世纪这里曾建过一座堡垒,现在到处都是残破的城墙基础,变成了四异。这是斗狮场;被观众席包围。下两层为包厢,底层为皇帝和外宾,上层为贵族;三楼为公务员;最上层是平民区:一共可以坐4万到5万人。狮子洞还在下一层,有直达场的通道。斗狮是一种刑罚,也可以说是一种审判:犯人摆在狮子面前,狮子与他搏斗;如果他真的杀了狮子,那么直道就在他身边,他可以自由了。当然,狮子吃得更多;这些人可能应得的。想到囚徒及其亲人的悲惨和恐怖,敌人的欢喜,皇帝的威严,以及广大观众好奇而紧张的脸庞,就像一场噩梦。
这个场地建于公元一世纪,最初是一个剧院,但后来被改建为斗狮场。狮子竞技场以南不远处是卡拉卡拉浴场。古罗马人对沐浴是相当讲究的,浴池都建得很好,而这一个更是华丽。整个地方都是用大理石建造的,并用镶嵌的石头铺成;有壁画、雕像和不寻常的器皿。房子很高,分上下两层,全部采用圆拱门,走进去感觉稳重;中心是一个带两个喷泉的大型健身房。该场占地六亩,可容纳1600人沐浴。浴池分为冷热蒸汽三种,各占一个房间。古罗马人来浴场不仅是为了洗澡;他们可以在这里谈生意,解决诉讼等等,就像我们去茶馆和餐馆一样。这里也有很多游戏。他们有空或累了就洗个澡,找几个朋友去游戏室消遣。不然就去客厅聊天,很“写意”。现在只剩下很多废墟了。还有很多大理石,已经搬来建造圣彼得教堂和其他教堂;博物馆里陈列着零星的物品。我们看到的只有一些雄伟的黄土骨头,站在阳光下,还有学者们仔细研究的“卡拉卡拉浴场”的照片。罗马自古以来就以其教堂而闻名。在康南海的《罗马之旅》、杜牧的诗《南朝四百八十寺,烟雨中有多少塔》中,情况有些相似;可惜去初夏的人,欣赏不了烟雨。圣彼得教堂最精美,在城北的尼罗河马戏团旧址上。
尼禄在这里杀死了许多基督徒。据说圣彼得被钉十字架后也葬在这里。这座教堂历经多次起起落落,现在的房子始建于16世纪初,经过了许多建筑师之手。七十二岁时,迈克尔·安吉洛奉保罗三世的命令在这里工作了十七年。后人认为是天使保罗的第三只假手为这座伟大的建筑设定了规模。以后虽然有增减,但一般都是以他为主。教堂内部以卡拉卡拉浴场为蓝本,许多高大的圆形拱门牢固地支撑着圆顶。教堂长六百九十六尺,宽四百五十尺,穹顶高四百零三尺,但乍看之下并没有那么大。因为我们平时看房子的大小,总是以室内的装饰物为标准,而装饰物的大小是有乐谱的。圣伯多禄堂的那本太大了,看不懂,“天使像巨人,鸽子像鹰”;所以一下子看清教堂的真实大小并不容易。但如果你看看里面走来的人,你会逐渐感觉到不同。教堂的墙壁是用彩色大理石建造的,还有许多用石头镶嵌的大型名画。大多数是亮蓝色和朱红色;与普通的教堂不同,它们明亮而富有。米开朗基罗雕刻的彼得雕像,温文尔雅,干净利落,别具一格,矗立在教堂的喇叭上。圣彼得教堂两侧的柱廊像两条手臂一样拥抱着圣彼得马戏团;场地中央是埃及济公方尖碑,左右两侧有大型喷泉。这两个回廊是亚历山大三世在十七世纪由佩尔尼尼建造的。
门廊内有四排多立克式石柱,共284根;场地左右两侧各有两块圆石。站在上面望着同侧的玄关,感觉只有一排柱子,气势更加雄伟。这个圆圈外面有一条弯曲的白石线,是梵蒂冈和意大利的分界线。教皇每年复活节都会站在圣彼得教堂的露台上祝福人们,据说里面人山人海。圣保罗教堂位于南部城市外。相传是圣保罗墓地遗址,也是好柱子。门前是一个方形的院落,四面的回廊全是用一整块石头凿成的大柱子,比圣彼得的两条回廊还要古朴。教堂的内部也很简单,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但中间的八十根花岗岩柱和末端的六根蜡石柱纵横排列,仿佛置身于人迹罕至的古老森林之中。柱子上方的墙壁上,有历代教皇的石镶嵌雕像,全部为圆形框架。教堂旁边还有一个小柱廊,建于十二世纪。门廊围成一个方形的院子,低矮的墙基上排列着两层不同颜色的细柱,有的还镶嵌着金色的玻璃块。此廊做工精细,可以说如湘绣,美不胜收却又如王羲之的书法。雄伟地矗立在市中心的威尼斯广场上,是曼努埃尔第二济公画廊。这是现代意大利的建筑,不乏实力。一条弯曲的走廊,在高大的石头地基上。前有三级石阶:一楼居中,二三楼分左右,通向门廊两端。
这个玄关左右上下对称,中间有弯道,有动静之美。从走廊前面的柱间望着暮色中的罗马城,感觉又远又宽。罗马艺术的瑰宝自然在梵蒂冈宫; Capitoline 博物馆中有一些,但与梵蒂冈相比太少了。梵蒂冈有几座雕塑馆,藏品约4000件,著名的“老古恩”就在这里。书院收藏的画作有五十幅,都是极好的。拉斐尔的《基督的显现》就是其中之一,但现在已关闭进行维修。梵蒂冈的壁画极其精彩,而且大多是拉斐尔及其弟子的手笔,是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有四个拉斐尔房间和一些门廊,里面装满了他们的财物。拉斐尔由此得名。他来自乌尔比诺,他的父亲是一位诗人和画家。到了罗马后,深受大家的喜爱,大家都想教他画画;他太忙了,只好收一些弟子做助理。他的专长是画人体。这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四肢丰满强壮,有骨有肉。这自然受到一些佛罗伦萨人的影响,但主要是他的天才。他还具有敏锐的节奏感、距离感、大小和色彩感,因此他成为了所有人。他在罗马居住的房子还在,他被安葬在国葬馆。修斯廷厅与拉斐尔厅齐名,也在宫中。这座神殿是十五世纪修司第四任酋长所建,宽一百三十三尺,宽四十五尺。两侧墙壁的上部由佛罗伦萨画家装饰,包括Potekili。屋顶上挂满了米开朗基罗的画作,奇斯廷厅在这里很有名。 Michael Angelo 是佛罗伦萨派的巅峰之作。
他画的不多,他的生活精髓就在这里。当他画这个屋顶时,他将一种深沉而庄重的情绪渗透到了这幅画中。他的构图节奏流畅,身体的轮廓也自然而含蓄,气势磅礴是他的独特优势。殿内祭坛的墙壁,也是他的巨幅画作,名为《最后的审判》。这幅壁画是多年后画的,他花了七年的时间。罗马城外有几条隧道,一世纪至五世纪被基督徒挖掘为坟墓,也用作礼拜场所。尼禄猎杀了经常在这里避难的基督徒。最值得一看的是圣卡利斯托隧道。还有一朵有十二瓣的虔诚花,据说代表十二使徒。我们正在看圣塞巴斯蒂安教堂下面的地方,每个人都点燃了小蜡烛,然后下楼。曲折的窄道两旁是深浅不一的墓葬;现在自然是空荡荡的,但有时还是能看到散落的白骨。有一个地方据说是圣彼得住过的地方,现在变成了一个壁龛,墙壁也画得很好。还有一些壁画遗迹。隧道好像有四层,占用空间很大。圣塞巴斯蒂安教堂里保存着一块石头,上面有两个大脚印;他们说这是耶稣基督的,现在在神殿里供奉。另一座教堂也提供这样的石头,据说是仿制品。小教堂建于五世纪,用来支撑一条绑在圣彼得身上的铁链。现在链条仍然在一个精致的壁龛里。殿内有几尊米凯·安杰洛雕刻的周立乌斯二碑上的雕像;摩西雕像特别有名。最初的坚定精神和勇敢的力量从眉毛、胡须、手臂、手、腿、处处流露出来,教你感觉自己遇到了一个伟大的人。
还有一座带有婴儿雕像的阿拉古里教堂。这个婴儿当然是耶稣基督。它是 15 世纪耶路撒冷的一位基督徒用橄榄木雕刻而成。他把它带到罗马并在这座教堂里献祭。全世界很多人都来许愿,据说很有效;上面挂着很多金银饰品,层层叠叠,都是别人做的。也有很多信写给它,表示钦佩。在罗马城的西南角,紧挨着古城墙的是英国墓地或新教墓地。埋葬在这里的人大多是艺术家和诗人,所以意大利人和其他国家的人终日前来瞻仰。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十九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和齐泽的坟墓。雪莱的心埋在英格兰,他的骨灰在这里。墓在古城墙下的斜坡上,上面覆盖着一块长方形的白石;第一排刻有“心的中心”,后两排是生卒年月,后三排是莎士比亚《风暴》中的仙歌。他没有受到任何伤害,但海涛改变了它,从此变得更加神奇。幸运的是,这正是雪莱的死和他的性格。离吉兹墓不远,上面刻着一块墓碑:这墓是英国年轻诗人的遗体;他的墓碑上刻着一句话:“这里躺着一个人,他的名字是用水写的。”最后一行表示快速腐烂;但他的名字就是所谓的“永不废河”,怎么可能?当时的预期。后来有人不作新的解释,就用这个行话写了一首诗,连子子的小雕像就嵌在他墓旁墙上的一块青铜里。这首诗的原文很有意思。 ziz有个好名字,据说是写在水里的;一滴一滴的水,后人的眼泪——英雄的泪水已死,难以如此动人。安睡吧,虽言泄密,高风自以为是。这个墓地是罗马诗意的角落;一些热爱罗马的人,即使不死在意大利,也会被埋葬在这座“永恒之城”的永恒角落里。电灯下,说说W的小说。

“他还在河南吗?C大学不错吧?”我随口问道。 “不,他去了美国。” “美国?怎么办?” “你觉得奇怪吗?——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给他发电报让他当助理。” “哦!是他学心理学的。那个地方!他一直在那里成绩好?——他很愿意回去吗?” “不一定。他走之前来北京,我请他去七新吃饭,他看起来很不高兴。“为什么?” “他觉得中国没有地方让他做事。”他才回来一年。 C大学没钱吧?” “他不仅没钱,还说他疯了!” “疯了!”我们默默对视,一时无话可说。记得第一次见到W的名字是在《新生活》杂志上,当时我在P大学念书,W也在。我在《新生》里看到的是他的小说;但是一个朋友告诉我他读了很多心理学的书,P大学图书馆里什么都读。他也读了很多文学作品。他说他一直在看书。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P大学的走廊里。大学宿舍,他和朋友一起散步。有人告诉我,这是W。微弯的背,黑黑的小脸,长头发,近视的眼睛,这是W。以后经常看他的文字,想起一个人喜欢他。有一次我拿了一个心理翻译,让朋友让他看,他一个一个给我改了几十条,从来没有放松了一句话。永远的耻辱和感激留在我的心中。我又想起了在杭州的那个晚上。他突然来看我。
他说他和P一起游泳了三天,明天一早去上海。他原本是山东人,但回到上海时,他要去美国。我问了哥伦比亚大学的Psychology, Philosophy, and Scientific Method,我知道这是一本知名期刊。但他说,往往一年都没有好文章,毫无意义。他说,最近有心理学家在英国开会,其中一些人发表了有趣的评论。他还随手用铅笔在桌上一本书的背面,写下了《哲学科学》的书名和出版地,说是新书,可以看。他说走。我带他去了酒店。见床上铺着一本《人间地理》,他随手捡起来翻了个身。他说那本小书很有名,很好。昏暗的电灯下,我们对视了一会儿,然后问了几句简单的话;我离开了。直到现在,都没有见过他。他去美国后,起初写了一些文字,但后来就消失了。他的名字,在普通人的心中,就像远方的一朵云。我还记得他。两三年后,我又在《文学日报》上看到他的另一首诗,写的带着一种明显的兴致。我只读过他的诗。我读过不少他的小说;最让我难忘的是《雨夜》,讲的是北京一个黄包车夫的生活。 W是理科生,应该很冷静,但他的小说很火。这是W.p也去了美国,不过很快就回来了。他在波提姆住了一段时间,经常能看到W。回国后,大热天,我和他聊起了南京清凉山的W。
他说 W 正在研究行为心理学。他几乎整天都在实验室里。他解剖了许多老鼠并研究了它们的行为。 P说他也愿意学心理学;但看到老鼠垂死的颤抖后,他握着刀的手却无法放开。所以不得不改变路线。而W则是“玩刀得逞”、“苦于野心”,p觉得遥不可及。 P还说W研究动物行为很长时间了,他看到它们的一生都只是那些生理欲望,比如食欲、性欲、他们玩的把戏,并没有什么大道理。 因此,推测人的生命没有必要有任何崇高的动机;我们必须首先承认我们是动物,是真实的人。 W确实是这样的人。 P说他也相信W的话;真的,P回国后的态度很不一样。虽然W只想做自己的人,但是却收获了P这样的信徒,他自己可能也没料到。 P告诉我W的爱情故事。是的,爱情故事! P说这是一个跟W学的日本人,后来他走了,事情就过去了。 P说话这么冷,不像我们想象的爱情故事! P还给我指了一段W在《未来》中的《月光》。这是一部关于一男一女趁着月光,在河边的空船上偷偷聊天的小说。那个女人是已婚女人。此时,四人不见踪影,两人谈得十分亲热。但是P说W太胆小了,所以这次密谈后,他放开了。这篇文章是 W 自己写的。虽然没有熊熊烈火那么热闹,但也有着不一样的意义。科学与文学,科学与爱情,这就是W。
“‘疯了’!”这一刻,我突然恍然大悟:“大概是这样吧?我想。人一冷一热都会发疯的。” “嗯,”p点头。 “其实,他不用担心中国与否,只是舍不得!” “是啊。W这次真的很不开心,K在美国向他借钱,这次去北京,一路狂奔,去向K要钱,K没钱,他也知道;他没想到钱会用,他就是想拿来骂他,据说是拍桌子骂他的!” “这跟他没关系,就跟写小说一样!哦,这是W。” P无语,但我想起了一件事:“W到美国后会有一封信吗?” “从长远来看,没有信。” 1926 年 7 月 20 日,白马湖。 (原载于《文学周刊》1926年8月1日第236期)
1923年8月的一个晚上,我和平叔在秦淮河上旅行;平叔是第一个来的,我又来了。我们雇了一个“七板”,在太阳落山月亮来的时候下船。就这样桨淅淅沥沥的声音——淅淅沥沥,我们开始领略秦淮河那玫瑰色历史摇曳的味道。秦淮河之舟,胜过北京万园、颐和园之舟,西湖之舟,扬州瘦西湖之舟。这些地方的船要么笨重,要么简陋而狭窄;没有一个能唤起乘客的情绪,就像秦淮河上的小船一样。秦淮河上的船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大船;另一种是大船。另一种是小船,也就是所谓的“七板”。这艘大船有一个宽大的舱口,可容纳二十或三十人。陈设着字画和光滑的红木家具,桌子上总是镶嵌着冰冷的大理石表面。窗玻璃雕刻得很精细,给人一种柔软的感觉。红色和蓝色玻璃反射在窗格中;玻璃上有精致的花纹,也相当赏心悦目。 “七板”的规模虽然没有大船那么大,但淡蓝色的铁轨和空荡荡的船舱也充满了人情味。最好的部分是在它的机舱前部。客舱的前部是甲板的一部分。其上有一弧形顶,两侧由稀疏的栏杆支撑。里面通常有两个藤椅。躺下,可以聊天,可以远眺,可以眺望河两岸的河屋。这在大船上也有,所以在小船上更清楚。小屋前的屋顶下,总是挂着灯笼;灯的数量、明暗、颜色的粗细和浓淡,都是不同的。但无论如何,总是给你一个灯笼。这个灯笼真的是最迷人的东西。夜幕降临,大大小小的船上都亮起了灯。
放射状的黄色散光从双层玻璃反射出来,映出一片朦胧的雾霾; . In this thin mist and ripples, listening to the leisurely intermittent sound of the paddle, who can not be led into his sweet dreams? I just worry too much, how can these big boats be able to carry them? We were talking vaguely about the splendid deeds of the Qinhuai River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s described in "Peach Blossom Fan" and "Banqiao Miscellaneous Notes". We are so fascinated. We seem to have seen the lanterns reflecting the water and painting the scene of Lingbo. So our ship has become a heavy load of history. We finally realized that the boats on the Qinhuai River, so Yali is more than other places, and it has a strange attraction, which is really caused by many historical images. The water of the Qinhuai River is blue and yin; it looks thick but not greasy, or is it condensed by the golden powder of the Six Dynasties? When we first got on the boat, the sky was still dark, and the rippling soft waves were so peaceful and euphemistic, which made us think of the water and the sky, but also longed for the realm of drunkenness and gold. When the lights are on, the gloomy ones become heavy: the dim water light is like a dream; the light that occasionally flickers is the eyes of the dream. We sat in front of the cabin, and because of the raised roof, it seemed that we were always walking forward with our heads held high; so we, drifting like the wind, looked at the boats moored in the comfortable bays, the revolving lights in the boats Such a person is like a lower world, far away, and it is like looking at flowers in the fog, all hazy. At this time, we had passed the Lishe Bridge and saw the East Gate. Along the way, intermittent singing was heard: some came from the prostitutes along the river, and some came from the boats on the river.
We know that those songs are just inherited words, mechanically emanating from the jerky voice; but they have been swayed by the breeze of the summer night and the swaying of the water, and they have reached us. When I heard it, it was not just their singing, but the whispers of the breeze and the river. So we had to be provoked, shocked, and drifted in this song. Turning from the East Gate to the Bay, you will soon arrive at the Dazhong Bridge. There are three bridge arches in the Dazhong Bridge, all of which are wide and big, like three gates; it makes us feel that our boat and the us in the boat are really colorless when we pass under the bridge. The bridge bricks are dark brown, indicating its long history; but they are all in good condition, which makes people too fascinated by the solid beauty of ancient works. There are houses with wooden walls on both sides of the bridge, should there be a street in the middle? These houses are all dilapidated, and the traces of smoke for many years have obscured the beauty of the past. I imagine that when the Qinhuai River was at its peak, a house was specially built on such a grand bridge, and it must be richly painted; it must be brightly lit at night. Now there is only darkness left! But the house built on the bridge, after all, allows us to imagine the prosperity of the past; After crossing the Dazhong Bridge, you will arrive at the Qinhuai River, where the moon and the lights are shining and singing all night; this is the true face of the Qinhuai River. Outside the Dazhong Bridge, it is suddenly empty and wide, which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dense rows of people on both sides of the bridge. At first glance, the sparse forest, the faint moon, and the blue sky against the blue sky are quite like the scene of a deserted river crossing. I don't believe it is the prosperous Qinhuai River. However, the dizzying lights in the river, the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painting boats, the melodious flute rhythm, and the squeaking of the huqin finally made us know the green Qinhuai water.
Here, the sky is more exposed, so we feel that the night is late; from the clear water shadow, we only feel the thin night - this is the night of the Qinhuai River. Outside the Dazhong Bridge, there was originally a Fucheng Bridge, which was the end of our travels in the mouth of the boatman, or the end of the prosperous Qinhuai River. My feet once stepped on the ridge of Fucheng Bridge, when I was thirteen or fourteen years old. But I have traveled the Qinhuai River twice, but I have never seen the face of the Fucheng Bridge; I know that there is always a future, but I often feel a little illusory. I think it's better not to see it. It was midsummer. After we got off the boat, the summer heat was gradually dissipated by the fresh evening coolness and the breeze on the river; when we arrived here, we suddenly became enlightened, and our body suddenly became lighter. I felt a new chill. The sunlight in Nanjing is probably not as violent as in Hangzhou; the summer nights of the West Lake are always hot and the water is boiling, but the water of the Qinhuai River is so cold and green. No matter how long your shadows are, and your singing is disturbed, it always seems to be separated by a thin layer of green veil; it is all so quiet and cold green. We got out of the Dazhong Bridge and couldn't walk half a mile, so the boatman rowed the boat aside, stopped the oars and let it run. He thought it was the climax of prosperity, and then it was desolation; so let us appreciate it for a while. He squatted quietly. He's used to seeing this scene, it's probably just a no-brainer. This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whether it is rising or falling, in short, it is higher than us. The river was very lively at that time; most of the boats were moored, and the other half were traveling on the water. The moored ones are all on the side near the city, and our boat is naturally caught in it.
Because this side is a little crowded, I feel that the other side is very sparse. As each boat passes over there, we can draw its light shadows and curving waves, on our minds; it is evidently empty, and evidently still.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singing and shrill huqin sounds everywhere, and there were indeed very few round throats. But that jerky, sharp and crisp tone can make people feel juvenile, rough and informal, and it is just what we want. Besides, it is more or less separated to listen to, because the imagination and desire are always more enjoyable to be beautiful; and the hustle and bustle of the competition, the unevenness of the inflection, the clutter of far and near, and the noise of the musical instruments, combine into another meaning. Harmony also makes us at a loss, such as walking with the strong wind. This is really because our hearts have been withered for a long time and become fragile; so if we occasionally moisten them, we will be crazy and unable to control ourselves. But Qinhuai River is really boring. That is, like the faces of people in a boat, whether they are moored with us, whether they pass by in front of our eyes, they are always blurry, even vague; Dirt is in vain. It's really thought-provoking. Where we moored, the lights were indistinct; but they were all yellow and hazy. Huang can't understand it anymore, and with the halo, it's even more impossible. The more lights there are, the more dizzy it will be; in the interlacing of stars like yellow, the Qinhuai River seems to be enveloped in a fog of light.光芒与雾气腾腾的晕着,什么都只剩了轮廓了;所以人面的详细的曲线,便消失于我们的眼底了。但灯光究竟夺不了那边的月色;灯光是浑的,月色是清的,在浑沌的灯光里,渗入了一派清辉,却真是奇迹!那晚月儿已瘦削了两三分。
她晚妆才罢,盈盈的上了柳梢头。天是蓝得可爱,仿佛一汪水似的;月儿便更出落得精神了。岸上原有三株两株的垂杨树,淡淡的影子,在水里摇曳着。它们那柔细的枝条浴着月光,就像一支支美人的臂膊,交互的缠着,挽着;又像是月儿披着的发。而月儿偶然也从它们的交叉处偷偷窥看我们,大有小姑娘怕羞的样子。岸上另有几株不知名的老树,光光的立着;在月光里照起来。却又俨然是精神矍铄的老人。远处——快到天际线了,才有一两片白云,亮得现出异彩,像美丽的贝壳一般。白云下便是黑黑的一带轮廓;是一条随意画的不规则的曲线。这一段光景,和河中的风味大异了。但灯与月竟能并存着,交融着,使月成了缠绵的月,灯射着渺渺的灵辉;这正是天之所以厚秦淮河,也正是天之所以厚我们了。这时却遇着了难解的纠纷。秦淮河上原有一种歌妓,是以歌为业的。从前都在茶舫上,唱些大曲之类。每日午后一时起;什么时候止,却忘记了。晚上照样也有一回。也在黄晕的灯光里。我从前过南京时,曾随着朋友去听过两次。因为茶舫里的人脸太多了,觉得不大适意,终于听不出所以然。前年听说歌妓被取缔了,不知怎的,颇涉想了几次——却想不出什么。这次到南京,先到茶舫上去看看,觉得颇是寂寥,令我无端的怅怅了。
不料她们却仍在秦淮河里挣扎着,不料她们竟会纠缠到我们,我于是很张皇了。她们也乘着“七板子”,她们总是坐在舱前的。舱前点着石油汽灯,光亮眩人眼目:坐在下面的,自然是纤毫毕见了——引诱客人们的力量,也便在此了。舱里躲着乐工等人,映着汽灯的余辉蠕动着;他们是永远不被注意的。每船的歌妓大约都是二人;天色一黑。她们的船就在大中桥外往来不息的兜生意。无论行着的船,泊着的船,都要来兜揽的。这都是我后来推想出来的。那晚不知怎样,忽然轮着我们的船了。我们的船好好的停着,一只歌舫划向我们来的;渐渐和我们的船并着了。铄铄的灯光逼得我们皱起了眉头;我们的风尘色全给它托出来了,这使我踧踖不安了。那时一个伙计跨过船来,拿着摊开的歌折,就近塞向我的手里,说,“点几出吧”!他跨过来的时候,我们船上似乎有许多眼光跟着。同时相近的别的船上也似乎有许多眼睛炯炯的向我们船上看着。我真窘了!我也装出大方的样子,向歌妓们瞥了一眼,但究竟是不成的!我勉强将那歌折翻了一翻,却不曾看清了几个字;便赶紧递还那伙计,一面不好意思地说,“不要,我们……不要。”他便塞给平伯。平伯掉转头去,摇手说,“不要!”那人还腻着不走。平伯又回过脸来,摇着头道,“不要!”于是那人重到我处。
我窘着再拒绝了他。他这才有所不屑似的走了。我的心立刻放下,如释了重负一般。我们就开始自白了。我说我受了道德律的压迫,拒绝了她们;心里似乎很抱歉的。这所谓抱歉,一面对于她们,一面对于我自己。她们于我们虽然没有很奢的希望;但总有些希望的。我们拒绝了她们,无论理由如何充足,却使她们的希望受了伤;这总有几分不做美了。这是我觉得很怅怅的。至于我自己,更有一种不足之感。我这时被四面的歌声诱惑了,降服了;但是远远的,远远的歌声总仿佛隔着重衣搔痒似的,越搔越搔不着痒处。我于是憧憬着贴耳的妙音了。在歌舫划来时,我的憧憬,变为盼望;我固执的盼望着,有如饥渴。虽然从浅薄的经验里,也能够推知,那贴耳的歌声,将剥去了一切的美妙;但一个平常的人像我的,谁愿凭了理性之力去丑化未来呢?我宁愿自己骗着了。不过我的社会感性是很敏锐的;我的思力能拆穿道德律的西洋镜,而我的感情却终于被它压服着,我于是有所顾忌了,尤其是在众目昭彰的时候。道德律的力,本来是民众赋予的;在民众的面前,自然更显出它的威严了。我这时一面盼望,一面却感到了两重的禁制:一,在通俗的意义上,接近妓者总算一种不正当的行为;二,妓是一种不健全的职业,我们对于她们,应有哀矜勿喜之心,不应赏玩的去听她们的歌。
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两种思想在我心里最为旺盛。她们暂时压倒了我的听歌的盼望,这便成就了我的灰色的拒绝。那时的心实在异常状态中,觉得颇是昏乱。歌舫去了,暂时宁靖之后,我的思绪又如潮涌了。两个相反的意思在我心头往复:卖歌和卖淫不同,听歌和狎妓不同,又干道德甚事? ——但是,但是,她们既被逼的以歌为业,她们的歌必无艺术味的;况她们的身世,我们究竟该同情的。所以拒绝倒也是正办。但这些意思终于不曾撇开我的听歌的盼望。它力量异常坚强;它总想将别的思绪踏在脚下。从这重重的争斗里,我感到了浓厚的不足之感。这不足之感使我的心盘旋不安,起坐都不安宁了。 well!我承认我是一个自私的人!平伯呢,却与我不同。他引周启明先生的诗,“因为我有妻子,所以我爱一切的女人,因为我有子女,所以我爱一切的孩子。”①
--------①原诗是,“我为了自己的儿女才爱小孩子,为了自己的妻才爱女人”,见《雪朝》第48页。他的意思可以见了。他因为推及的同情,爱着那些歌妓,并且尊重着她们,所以拒绝了她们。在这种情形下,他自然以为听歌是对于她们的一种侮辱。但他也是想听歌的,虽然不和我一样,所以在他的心中,当然也有一番小小的争斗;争斗的结果,是同情胜了。至于道德律,在他是没有什么的;因为他很有蔑视一切的倾向,民众的力量在他是不大觉着的。这时他的心意的活动比较简单,又比较松弱,故事后还怡然自若;我却不能了。这里平伯又比我高了。在我们谈话中间,又来了两只歌舫。伙计照前一样的请我们点戏,我们照前一样的拒绝了。我受了三次窘,心里的不安更甚了。清艳的夜景也为之减色。船夫大约因为要赶第二趟生意,催着我们回去;我们无可无不可的答应了。我们渐渐和那些晕黄的灯光远了,只有些月色冷清清的随着我们的归舟。我们的船竟没个伴儿,秦淮河的夜正长哩!到大中桥近处,才遇着一只来船。这是一只载妓的板船,黑漆漆的没有一点光。船头上坐着一个妓女;暗里看出,白地小花的衫子,黑的下衣。她手里拉着胡琴,口里唱着青衫的调子。她唱得响亮而圆转;当她的船箭一般驶过去时,余音还袅袅的在我们耳际,使我们倾听而向往。
想不到在弩末的游踪里,还能领略到这样的清歌!这时船过大中桥了,森森的水影,如黑暗张着巨口,要将我们的船吞了下去,我们回顾那渺渺的黄光,不胜依恋之情;我们感到了寂寞了!这一段地方夜色甚浓,又有两头的灯火招邀着;桥外的灯火不用说了,过了桥另有东关头疏疏的灯火。我们忽然仰头看见依人的素月,不觉深悔归来之早了!走过东关头,有一两只大船湾泊着,又有几只船向我们来着。嚣嚣的一阵歌声人语,仿佛笑我们无伴的孤舟哩。东关头转湾,河上的夜色更浓了;临水的妓楼上,时时从帘缝里射出一线一线的灯光;仿佛黑暗从酣睡里眨了一眨眼。我们默然的对着,静听那汩——汩的桨声,几乎要入睡了;朦胧里却温寻着适才的繁华的余味。我那不安的心在静里愈显活跃了!这时我们都有了不足之感,而我的更其浓厚。我们却只不愿回去,于是只能由懊悔而怅惘了。船里便满载着怅惘了。直到利涉桥下,微微嘈杂的人声,才使我豁然一惊;那光景却又不同。右岸的河房里,都大开了窗户,里面亮着晃晃的电灯,电灯的光射到水上,蜿蜒曲折,闪闪不息,正如跳舞着的仙女的臂膊。我们的船已在她的臂膊里了;如睡在摇篮里一样,倦了的我们便又入梦了。那电灯下的人物,只觉像蚂蚁一般,更不去萦念。
这是最后的梦;可惜是最短的梦!黑暗重复落在我们面前,我们看见傍岸的空船上一星两星的,枯燥无力又摇摇不定的灯光。我们的梦醒了,我们知道就要上岸了;我们心里充满了幻灭的情思。1923年10月11日作完,于温州。(原载1924年1月25日《东方杂志》第21卷第2号20周年纪念号)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月亮渐渐地升高了,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妻在屋里拍着闰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沿着荷塘,是一条曲折的小煤屑路。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蓊蓊郁郁的。路的一旁,是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没有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脉脉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一旁,漏着几段空隙,像是特为月光留下的。树色一例是阴阴的,乍看像一团烟雾;但杨柳的丰姿,便在烟雾里也辨得出。
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只有些大意罢了。树缝里也漏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采的,是渴睡人的眼。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从诗歌里可以约略知道。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她们是荡着小船,唱着艳歌去的。采莲人不用说很多,还有看采莲的人。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梁元帝《采莲赋》里说得好:于是妖童媛女,荡舟心许;鷁首徐回,兼传羽杯;欋将移而藻挂,船欲动而萍开。尔其纤腰束素,迁延顾步;夏始春余,叶嫩花初,恐沾裳而浅笑,畏倾船而敛裾。可见当时嬉游的光景了。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于是又记起《西洲曲》里的句子: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今晚若有采莲人,这儿的莲花也算得“过人头”了;只不见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行的。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这样想着,猛一抬头,不觉已是自己的门前;轻轻地推门进去,什么声息也没有,妻已睡熟好久了。1927年7月,北京清华园。(原载1927年7月10日《小说月报》第18卷第7期)
我第一次与圣陶见面是在民国十年的秋天。那时刘延陵兄介绍我到吴淞炮台湾中国公学教书。到了那边,他就和我说:“叶圣陶也在这儿。”我们都念过圣陶的小说,所以他这样告我。我好奇地问道:“怎样一个人?”出乎我的意外,他回答我:“一位老先生哩。”但是延陵和我去访问圣陶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年纪并不老,只那朴实的服色和沉默的风度与我们平日所想象的苏州少年文人叶圣陶不甚符合罢了。记得见面的那一天是一个阴天。我见了生人照例说不出话;圣陶似乎也如此。我们只谈了几句关于作品的泛泛的意见,便告辞了。延陵告诉我每星期六圣陶总回甪直去;他很爱他的家。他在校时常邀延陵出去散步;我因与他不熟,只独自坐在屋里。不久,中国公学忽然起了风潮。我向延陵说起一个强硬的办法;——实在是一个笨而无聊的办法!——我说只怕叶圣陶未必赞成。但是出乎我的意外,他居然赞成了!后来细想他许是有意优容我们吧;这真是老大哥的态度呢。我们的办法天然是失败了,风潮延宕下去;于是大家都住到上海来。我和圣陶差不多天天见面;同时又认识了西谛,予同诸兄。这样经过了一个月;这一个月实在是我的很好的日子。我看出圣陶始终是个寡言的人。大家聚谈的时候,他总是坐在那里听着。
他却并不是喜欢孤独,他似乎老是那么有味地听着。至于与人独对的时候,自然多少要说些话;但辩论是不来的。他觉得辩论要开始了,往往微笑着说:“这个弄不大清楚了。”这样就过去了。他又是个极和易的人,轻易看不见他的怒色。他辛辛苦苦保存着的《晨报》副张,上面有他自己的文字的,特地从家里捎来给我看;让我随便放在一个书架上,给散失了。当他和我同时发见这件事时,他只略露惋惜的颜色,随即说:“由他去末哉,由他去末哉!”我是至今惭愧着,因为我知道他作文是不留稿的。他的和易出于天性,并非阅历世故,矫揉造作而成。他对于世间妥协的精神是极厌恨的。在这一月中,我看见他发过一次怒;——始终我只看见他发过这一次怒——那便是对于风潮的妥协论者的蔑视。风潮结束了,我到杭州教书。那边学校当局要我约圣陶去。圣陶来信说:“我们要痛痛快快游西湖,不管这是冬天。”他来了,教我上车站去接。我知道他到了车站这一类地方,是会觉得寂寞的。他的家实在太好了,他的衣着,一向都是家里管。我常想,他好像一个小孩子;像小孩子的天真,也像小孩子的离不开家里人。必须离开家里人时,他也得找些熟朋友伴着;孤独在他简直是有些可怕的。所以他到校时,本来是独住一屋的,却愿意将那间屋做我们两人的卧室,而将我那间做书室。
这样可以常常相伴;我自然也乐意,我们不时到西湖边去;有时下湖,有时只喝喝酒。在校时各据一桌,我只预备功课,他却老是写小说和童话。初到时,学校当局来看过他。第二天,我问他,“要不要去看看他们?”他皱眉道:“一定要去么?等一天吧。”后来始终没有去。他是最反对形式主义的。那时他小说的材料,是旧日的储积;童话的材料有时却是片刻的感兴。如《稻草人》中《大喉咙》一篇便是。那天早上,我们都醒在床上,听见工厂的汽笛;他便说:“今天又有一篇了,我已经想好了,来的真快呵。”那篇的艺术很巧,谁想他只是片刻的构思呢!他写文字时,往往拈笔伸纸,便手不停挥地写下去,开始及中间,停笔踌躇时绝少。他的稿子极清楚,每页至多只有三五个涂改的字。他说他从来是这样的。每篇写毕,我自然先睹为快;他往往称述结尾的适宜,他说对于结尾是有些把握的。看完,他立即封寄《小说月报》;照例用平信寄。我总劝他挂号;但他说:“我老是这样的。”他在杭州不过两个月,写的真不少,教人羡慕不已。《火灾》里从《饭》起到《风潮》这七篇,还有《稻草人》中一部分,都是那时我亲眼看他写的。在杭州待了两个月,放寒假前,他便匆匆地回去了;他实在离不开家,临去时让我告诉学校当局,无论如何不回来了。
但他却到北平住了半年,也是朋友拉去的。我前些日子偶翻十一年的《晨报副刊》,看见他那时途中思家的小诗,重念了两遍,觉得怪有意思。北平回去不久,便入了商务印书馆编译部,家也搬到上海。从此在上海待下去,直到现在——中间又被朋友拉到福州一次,有一篇《将离》抒写那回的别恨,是缠绵悱恻的文字。这些日子,我在浙江乱跑,有时到上海小住,他常请了假和我各处玩儿或喝酒。有一回,我便住在他家,但我到上海,总爱出门,因此他老说没有能畅谈;他写信给我,老说这回来要畅谈几天才行。十六年一月,我接眷北来,路过上海,许多熟朋友和我饯行,圣陶也在。那晚我们痛快地喝酒,发议论;他是照例地默着。酒喝完了,又去乱走,他也跟着。到了一处,朋友们和他开了个小玩笑;他脸上略露窘意,但仍微笑地默着。圣陶不是个浪漫的人;在一种意义上,他正是延陵所说的“老先生”。但他能了解别人,能谅解别人,他自己也能“作达”,所以仍然——也许格外——是可亲的。那晚快夜半了,走过爱多亚路,他向我诵周美成的词,“酒已都醒,如何消夜永!”我没有说什么;那时的心情,大约也不能说什么的。我们到一品香又消磨了半夜。这一回特别对不起圣陶;他是不能少睡觉的人。他家虽住在上海,而起居还依着乡居的日子;早七点起,晚九点睡。
有一回我九点十分去,他家已熄了灯,关好门了。这种自然的,有秩序的生活是对的。那晚上伯祥说:“圣兄明天要不舒服了。”想起来真是不知要怎样感谢才好。第二天我便上船走了,一眨眼三年半,没有上南方去。信也很少,却全是我的懒。我只能从圣陶的小说里看出他心境的迁变;这个我要留在另一文中说。圣陶这几年里似乎到十字街头走过一趟,但现在怎么样呢?我却不甚了然。他从前晚饭时总喝点酒,“以半醺为度”;近来不大能喝酒了,却学了吹笛——前些日子说已会一出《八阳》,现在该又会了别的了吧。他本来喜欢看看电影,现在又喜欢听听昆曲了。但这些都不是“厌世”,如或人所说的;圣陶是不会厌世的,我知道。又,他虽会喝酒,加上吹笛,却不曾抽什么“上等的纸烟”,也不曾住过什么“小小别墅”,如或人所想的,这个我也知道。1930年7月,北平清华园。伦敦卖旧书的铺子,集中在切林克拉斯路(CharingCrossRoad);那是热闹地方,顶容易找。路不宽,也不长,只这么弯弯的一段儿;两旁不短的是书,玻璃窗里齐整整排着的,门口摊儿上乱哄哄摆着的,都有。加上那徘徊在窗前的,围绕着摊儿的,看书的人,到处显得拥拥挤挤,看过去路便更窄了。摊儿上看最痛快,随你翻,用不着“劳驾”“多谢”;可是让风吹日晒的到底没什么好书,要看好的还得进铺子去。
进去了有时也可随便看,随便翻,但用得着“劳驾”“多谢”的时候也有;不过爱买不买,决不至于遭白眼。说是旧书,新书可也有的是;只是来者多数为的旧书罢了。最大的一家要算福也尔(foyle),在路西;新旧大楼隔着一道小街相对着,共占七号门牌,都是四层,旧大楼还带地下室——可并不是地窨子。店里按着书的性质分二十五部;地下室里满是旧文学书。这爿店二十八年前本是一家小铺子,只用了一个店员;现在店员差不多到了二百人,藏书到了二百万种,伦敦的《晨报》称为“世界最大的新旧书店”。两边店门口也摆着书摊儿,可是比别家的大。我的一本《袖珍欧洲指南》,就在这儿从那穿了满染着书尘的工作衣的店员手里,用半价买到的。在摊儿上翻书的时候,往往看不见店员的影子;等到选好了书四面找他,他却从不知那一个角落里钻出来了。但最值得流连的还是那间地下室;那儿有好多排书架子,地上还东一堆西一堆的。乍进去,好像掉在书海里;慢慢地才找出道儿来。屋里不够亮,土又多,离窗户远些的地方,白日也得开灯。可是看得自在;他们是早七点到晚九点,你待个几点钟不在乎,一天去几趟也不在乎。只有一件,不可着急。你得像逛庙会逛小市那样,一半玩儿,一半当真,翻翻看看,看看翻翻;也许好几回碰不见一本合意的书,也许霎时间到手了不止一本。
开铺子少不了生意经,福也尔的却颇高雅。他们在旧大楼的四层上留出一间美术馆,不时地展览一些画。去看不花钱,还送展览目录;目录后面印着几行字,告诉你要买美术书可到馆旁艺术部去。展览的画也并不坏,有卖的,有不卖的。他们又常在馆里举行演讲会,讲的人和主席的人当中,不缺少知名的。听讲也不用花钱;只每季的演讲程序表下,“恭请你注意组织演讲会的福也尔书店”。还有所谓文学午餐会,记得也在馆里。他们请一两个小名人做主角,随便谁,纳了餐费便可加入;英国的午餐很简单,费不会多。假使有闲工夫,去领略领略那名隽的谈吐,倒也值得的,不过去的却并不怎样多。牛津街是伦敦的东西通衢,繁华无比,街上呢绒店最多;但也有一家大书铺,叫做彭勃思(Bumpus)的便是。这铺子开设于一七九○年左右,原在别处;一八五○年在牛津街开了一个分店,十九世纪末便全挪到那边去了,维多利亚时代,店主多马斯彭勃思很通声气,来往的有迭更斯,兰姆,麦考莱,威治威斯等人;铺子就在这时候出了名。店后本连着旧法院,有看守所,守卫室等,十几年来都让店里给买下了。这点古迹增加了人对于书店的趣味。法院的会议圆厅现在专作书籍展览会之用;守卫室陈列插图的书,看守所变成新书的货栈。
但当日的光景还可从一些画里看出:如十八世纪罗兰生(Rowlandson)所画守卫室内部,是晚上各守卫提了灯准备去查监的情形,瞧着很忙碌的样子。再有一个图,画的是一七二九的一个守卫,神气够凶的。看守所也有一幅画,砖砌的一重重大拱门,石板铺的地,看守室的厚木板门严严锁着,只留下一个小方窗,还用十字形的铁条界着;真是铜墙铁壁,插翅也飞不出去。这家铺子是五层大楼,却没有福也尔家地方大。下层卖新书,三楼卖儿童书,外国书,四楼五楼卖廉价书;二楼卖绝版书,难得的本子,精装的新书,还有《圣经》,祈祷书,书影等等,似乎是菁华所在。他们有初印本,精印本,著者自印本,著者签字本等目录,搜罗甚博,福也尔家所不及。新书用小牛皮或摩洛哥皮(山羊皮——羊皮也可仿制)装订,烫上金色或别种颜色的立体派图案;稀疏的几条平直线或弧线,还有“点儿”,错综着配置,透出干净,利落,平静,显豁,看了心目清朗。装订的书,数这儿讲究,别家书店里少见。书影是仿中世纪的抄本的一叶,大抵是祷文之类。中世纪抄本用黑色花体字,文首第一字母和叶边空处,常用蓝色金色画上各种花饰,典丽矞皇,穷极工巧,而又经久不变;仿本自然说不上这些,只取其也有一点古色古香罢了。
一九三一年里,这铺子举行过两回展览会,一回是剑桥书籍展览,一回是近代插图书籍展览,都在那“会议厅”里。重要的自然是第一回。牛津剑桥是英国最著名的大学;各有印刷所,也都著名。这里从前展览过牛津书籍,现在再展览剑桥的,可谓无遗憾了。这一年是剑桥目下的辟特印刷所(ThePittPress)奠基百年纪念,展览会便为的庆祝这个。展览会由鼎鼎大名的斯密兹将军(GeneralSmuts)开幕,到者有科学家詹姆士金斯(JamesJeans),亚特爱丁顿(ArthurEddington),还有别的人。展览分两部,现在出版的书约莫四千册是一类;另一类是历史部分。剑桥的书字型清晰,墨色匀称,行款合式,书扉和书衣上最见工夫;尤其擅长的是算学书,专门的科学书。这两种书需要极精密的技巧,极仔细的校对;剑桥是第一把手。但是这些东西,还有他们印的那些冷僻的外国语书,都卖得少,赚不了钱。除了是大学印刷所,别家大概很少愿意承印。剑桥又承印《圣经》;英国准印《圣经》的只剑桥牛津和王家印刷人。斯密兹说剑桥就靠《圣经》和教科书赚钱。可是《泰晤士报》社论中说现在印《圣经》的责任重大,认真地考究地印,也只能够本罢了。——一五八八年英国最早的《圣经》便是由剑桥承印的。
英国印第一本书,出于伦敦威廉甲克司登(WilliamCaxton)之手,那是一四七七年。到了一五二一,约翰席勃齐(JohnSiberch)来到剑桥,一年内印了八本书,剑桥印刷事业才创始。八年之后,大学方面因为有一家书纸店与异端的新教派勾结,怕他们利用书籍宣传,便呈请政府,求英王核准,在剑桥只许有三家书铺,让他们宣誓不卖未经大学检查员审定的书。那时英王是亨利第八;一五三四年颁给他们勅书,授权他们选三家书纸店兼印刷人,或书铺,“印行大学校长或他的代理人等所审定的各种书籍”。这便是剑桥印书的法律根据。不过直到一五八三年,他们才真正印起书来。那时伦敦各家书纸店有印书的专利权,任意抬高价钱。他们妒忌剑桥印书,更恨的是卖得贱。恰好一六二○年剑桥翻印了他们一本文法书,他们就在法庭告了一状。剑桥师生老早不乐意他们抬价钱,这一来更愤愤不平;大学副校长第二年乘英王詹姆士第一上新市场去,半路上就递上一件呈子,附了一个比较价目表。这样小题大做,真有些书呆子气。王和诸大臣商议了一下,批道,我们现在事情很多,没工夫讨论大学与诸家书纸店的权益;但准大学印刷人出售那些文法书,以救济他的支绌。这算是碰了个软钉子,可也算是胜利。
那呈子,那批,和上文说的那本《圣经》都在这一回展览中。席勃齐印的八本书也有两种在这里。此外还有一六二九年初印的定本《圣经》,书扉雕刻繁细,手艺精工之极。又密尔顿《力息达斯》(Lycidas)的初本也在展览着,那是经他亲手校改过的。近代插图书籍展览,在圣诞节前不久,大约是让做父母的给孩子们多买点节礼吧。但在一个外国人,却也值得看看。展览的是七十年来的作品,虽没有什么系统,在这里却可以找着各种美,各种趋势。插图与装饰画不一样,得吟味原书的文字,透出自己的机锋。心要灵,手要熟,二者不可缺一。或实写,或想象,因原书情境,画人性习而异。——童话的插图却只得凭空着笔,想象更自由些;在不自由的成人看来,也许别有一种滋味。看过赵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里谭尼尔(JohnTenniel)的插画的,当会有同感吧。——所展览的,幽默,秀美,粗豪,典重,各擅胜场,琳琅满目;有人称为“视觉的音乐”,颇为近之。最有味的,同一作家,各家插画所表现的却大不相同。譬如莪默伽亚谟(OmarKhayyam),莎士比亚,几乎在一个人手里一个样子;展览会里书多,比较着看方便,可以扩充眼界。插图有“黑白”的,有彩色的;“黑白”的多,为的省事省钱。
就黑白画而论,从前是雕版,后来是照相;照相虽然精细,可是失掉了那种生力,只要拿原稿对看就会觉出。这儿也展览原稿,或是灰笔画,或是水彩画;不但可以“对看”,也可以让那些艺术家更和我们接近些。《观察报》记者记这回展览会,说插图的书,字往往印得特别大,意在和谐;却实在不便看。他主张书与图分开,字还照寻常大小印。他自然指大本子而言。但那种“和谐”其实也可爱;若说不便,这种书原是让你慢慢玩赏的,那能像读报一样目下数行呢?再说,将配好了的对儿生生拆开,不但大小不称,怕还要多花钱。诗籍铺(ThePoetryBookshop)真是米米小,在一个大地方的一道小街上。“叫名”街,实在一条小胡同吧。门前不大见车马,不说;就是行人,一天也只寥寥几个。那道街斜对着无人不知的大英博物院;街口钉着小小的一块字号木牌。初次去时,人家教在博物院左近找。问院门口守卫,他不知道有这个铺子,问路上戴着常礼帽的老者,他想没有这么一个铺子;好容易才找着那块小木牌,真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这铺子从前在另一处,那才冷僻,连裴歹克的地图上都没名字,据说那儿是一所老宅子,才真够诗味,挪到现在这样平常的地带,未免太可惜。那时候美国游客常去,一个原因许是美国看不见那样老宅子。
诗人赫洛德孟罗(HaroldMonro)在一九一二年创办了这爿诗籍铺。用意在让诗与社会发生点切实的关系。孟罗是二十多年来伦敦文学生涯里一个要紧角色。从一九一一给诗社办《诗刊》(PoetryReview)起知名。在第一期里,他说,“诗与人生的关系得再认真讨论,用于别种艺术的标准也该用于诗。”他觉得能做诗的该做诗,有困难时该帮助他,让他能做下去;一般人也该念诗,受用诗。为了前一件,他要自办杂志,为了后一件,他要办读诗会;为了这两件,他办了诗籍铺。这铺子印行过《乔治诗选》(GeorgianPoetry),乔治是现在英王的名字,意思就是当代诗选,所收的都是代表作家。第一册出版,一时风靡,买诗念诗的都多了起来;社会确乎大受影响。诗选共五册;出第五册时在一九二二,那时乔治诗人的诗兴却渐渐衰了。一九一九到二五年铺子里又印行《市本》月刊(TheChapbook)登载诗歌,评论,木刻等,颇多新进作家。读诗会也在铺子里;星期四晚上准六点钟起,在一间小楼上。一年中也有些时候定好了没有。从创始以来,差不多没有间断过。前前后后著名的诗人几乎都在这儿读过诗:他们自己的诗,或他们喜欢的诗。入场券六便士,在英国算贱,合四五毛钱。
在伦敦的时候,也去过两回。那时孟罗病了,不大能问事,铺子里颇为黯淡。两回都是他夫人爱立达克莱曼答斯基(AlidaKlementaski)读,说是找不着别人。那问小楼也容得下四五十位子,两回去,人都不少;第二回满了座,而且几乎都是女人——还有挨着墙站着听的。屋内只读诗的人小桌上一盏蓝罩子的桌灯亮着,幽幽的。她读济兹和别人的诗,读得很好,口齿既清楚,又有顿挫,内行说,能表出原诗的情味。英国诗有两种读法,将每个重音咬得清清楚楚,顿挫的地方用力,和说话的调子不相像,约翰德林瓦特(JohnDrinkwater)便主张这一种。他说,读诗若用说话的调子,太随便,诗会跑了。但是参用一点儿,像克莱曼答斯基女士那样,也似乎自然流利,别有味道。这怕要看什么样的诗,什么样的读诗人,不可一概而论。但英国读诗,除不吟而诵,与中国根本不同之处,还有一件:他们按着文气停顿,不按着行,也不一定按着韵脚。这因为他们的诗以轻重为节奏,文句组织又不同,往往一句跨两行三行,却非作一句读不可,韵脚便只得轻轻地滑过去。读诗是一种才能,但也需要训练;他们注重这个,训练的机会多,所以是诗人都能来一手。铺子在楼下,只一间,可是和读诗那座楼远隔着一条甬道。
屋子有点黑,四壁是书架,中间桌上放着些诗歌篇子(Sheets),木刻画。篇子有宽长两种,印着诗歌,加上些零星的彩画,是给大人和孩子玩儿的。犄角儿上一张帐桌子,坐着一个戴近视眼镜的,和蔼可亲的,圆脸的中年妇人。桌前装着火炉,炉旁蹲着一只大白狮子猫,和女人一样胖。有时也遇见克莱曼答斯基女士,匆匆地来匆匆地去。孟罗死在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五日。第二天晚上到铺子里去,看见两个年轻人在和那女人司帐说话;说到诗,说到人生,都是哀悼孟罗的。话音很悲伤,却如清泉流泻,差不多句句像诗;女司帐说不出什么,唯唯而已。孟罗在日最尽力于诗人文人的结合,他老让各色的才人聚在一块儿。又好客,
家里炉旁(英国终年有用火炉的时候)常有许多人聚谈,到深夜才去。这两位青年的伤感不是偶然的。他的铺子可是赚不了钱;死后由他夫人接手,勉强张罗,现在许还开着。1934年10月27日作。(原载1935年1月1日《中学生》第51号)
文:小刀

